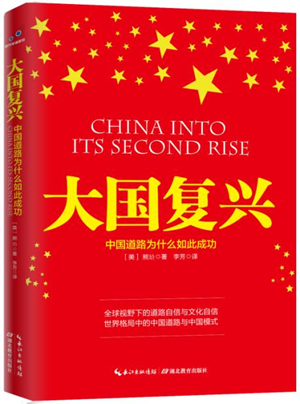
虽然已是八十岁高龄,但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近期很是活跃。去年,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由熊玠主编的《习近平时代》(英文版)高调上市,纽约时报的整版广告,美国高层政要、跨国公司CEO、美国大型智库、联合国成员代表处等,共一千多人收到赠书,在美国主流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今年3月份,他的新书《大国复兴》又在大陆出版。
2006年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总结、探讨西方主要国家的崛起之路,引发广泛热议,随之出版的同名图书至今依然畅销各大书店。压抑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民,更期盼的话题当然是“中国崛起”。按熊玠的说法,公元713年-1820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强国,是谓第一次崛起,而《大国复兴》主要是讲述当下的中国,是谓第二次崛起。该书英文版的书名其实是最好的注解(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凤凰涅槃,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机会再次来临。这种“反转式”崛起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崛起有显著不同。在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曾经站在世界之巅,并在长期衰败之后再度走向复兴。
本书视野广阔,视角独特。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著仅仅将中国视为普通国家,却忽略了其绵延至今的文明及其对当代的影响。因此很少有论著将中国传统与当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有机地整合起来加以讨论。鉴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作者认为理应去探寻其长寿的原因,以便了解过去与现在是如何相互联系,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现实。同样,很少有关于中国的著作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全面分析中国的现实,而在其中,几乎没有将现在的发展视为中国的复兴,更不用说将其与第一次崛起作比较并从百年屈辱史中吸取教训。熊玠正是从中国第一次崛起的历史出发,探讨中国第二次崛起中出现的问题,这个独特的研究角度,使该书具有了更为宽阔的全球视野,显得与众不同
中华文明为何长寿?作者认为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华文明比其他古文明存活更久,甚至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自我调整,这些要素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生态地理因素、半宗教因素(如“天”)以及历史的巧合(如封建制度早于专制国家的建立),这些要素使中华文明在影响黄河流域以外的族群并使其融入汉族文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类因素包括统一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和沿用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保证了朝代在更替中延续中国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而导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其自身的包容性,以及其兼容并蓄的能力。
举例来说,正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使得丝绸之路两端的两个大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命运,西罗马在蛮族的入侵中走向灭亡,迈入漫长的中世纪,而中国经过几百年的民族大融合,最终,“和同为一家”,在唐朝开元年间第一次崛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中华文明近代何以衰落?在作者看来,清朝在近代走向封闭,尽管它在极尽可能地实现自我完善,却没有创新。它不知道遥远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文明,因此在中西文明发生碰撞时,便不可避免地一触即溃。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本质上是农耕文明相对工业文明的衰落。
中国为何能够再次崛起?这首先在于重拾“兼容并蓄”传统。中国在儒家文化崩坏后,迅速转向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继而接受市场经济,并逐渐发展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说兼容并蓄是优秀传统,那么改革开放就是这种特质在新时代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古今结合、中西合璧是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国家主导经济的传统。这一传统最早可追溯到汉朝早期的盐铁专卖。国家主导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同时,大型国有企业承担了私人中小型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建设的主要维护成本;最后,庞大人口支持下的规模经济、后发国家优势、和平的发展环境、外向型的经济等也是中国复兴之路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全面驳斥了“中国威胁论”。除了探寻中华文明再次崛起的根源外,驳斥“中国威胁论”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随着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二,一些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中国威胁论”又有了它的土壤。作者认为,这种“不自信”又“盲目”的态度,也能够很好说明问题。
评价中国应该跳出固有的政治传统。西方一些现实主义者担心“中国威胁”只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的经验,认为后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严重失衡,例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等等。但问题在于,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崛起的国家。
中国的第一次崛起是和平崛起,并未滥用权势。在作者看来,中国第一次崛起能够如此和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文化的。第一,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广泛分布的河流航道以及水系的支持,除了能够自给自足外还有所盈余,这就使得中国无需转向海外市场以获取更多资源,也没有建立殖民地和以其他形式扩张的需要和野心。第二是文化原因,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相信以“王道”而非“霸道”服众。谨记这一不滥用权力的传统,就能更好地推测中国在复兴时的表现。
中国在近代受尽了外国列强的屈辱。所以当这些积压已久的对外国强权不公正的愤怒一旦爆发,便给予了中国人强烈地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愿望,并使其深深地同情世界上那些被肆意践踏的国家。在熊玠看来,这正是中国从衰落的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所以在1944年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时候,由于中国的坚持,宪章第二条第三款中才将“正义”一词写入。
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总的来说,本书通过聚焦中华文明的第一次崛起直至19世纪中叶的衰落,来剖析中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复兴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反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反沙文主义,正是这新秩序的特质。除此之外,根基于中华文明基础上的“以大事小”,也是重要表现。如中国对非洲及其他落后地区无偿贷款及赦免债务等都是体现。这正是中国崛起所蕴含的“和平”文化基因,对世界现有秩序并不是威胁。马丁 雅克所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等观点,熊玠并不认同。
本书虽然名为《大国复兴》,但熊玠似乎并不打算过多讨论中国会不会复兴、为什么能复兴,而是把复兴当成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而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GDP最晚于2035年赶上美国,之后至少20年内拥有与美国相称的军事实力,这正是熊玠在书中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