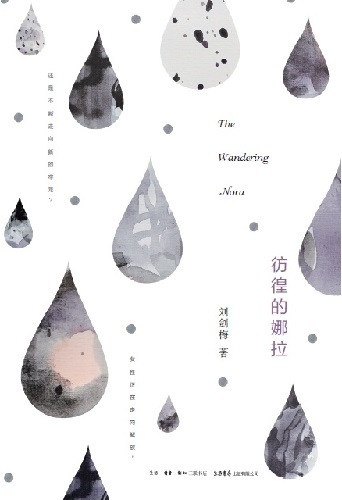
1879年,易卜生《玩偶之家》首演,“娜拉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发声一问,“娜拉走后怎样?”
1962年,银幕上的李双双,为自己争取在家庭和社会的平等权利。
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过半,中国女性的身、心、灵,是否已收获安顿?
继前一本散文集《狂欢的女神》后,时隔八年,刘剑梅再次结集女性主义思考的续篇《彷徨的娜拉》近日由三联生活书店出版。刘再复先生特地为该书作序,评价这部作品依然是在“用女性视角观察社会、观察人生,为女性说话、为女性请命”。
将新书命名为《彷徨的娜拉》,显然是与前作对应。相较于《狂欢的女神》呈现出的浪漫与激情,《彷徨的娜拉》倾向于哈姆雷特特型,直面现实的困境以及人生的种种无奈。两部作品创作之间,作者由青年步入中年,从狂欢到彷徨,从浪漫到现实。作者以女性主义立场,审视、反思两个主题: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定义,以及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中,女性种种身份的撕扯。
书中,刘剑梅抛出实质性提问:当下中国女性生存状态进步与否?
《彷徨的娜拉》针对国内社会当前的女性生存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沉淀出更深层次的关照。与近一个世纪前的妇女解放、走出家庭相对立,当今社会的女性更多“掉过头来,转回家去,重新进入男人的‘樊笼’,追逐男人所设置的铜墙铁壁”。抛弃女性的独立与尊严,依附于“安乐窝”,“严重缺乏主体性”。有家庭的事业女性更是陷入社会义务和家庭义务的双重压力之中。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益发严苛,而这种困局恐将一直持续下去。相比“狂欢”的瞬间,“彷徨”更是生活的常态。
在序言中,刘剑梅说自己迷恋“翅膀”的意象,她引用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巨翅老人》:老态龙钟的天使拥有一副翅膀,被众人视作怪物,故事的末尾,他还是飞离了这个不值得留念的,充满欲念的人间。有评论认为,羽毛残破的翅膀,就如同女性主体性的隐喻,它必然伴随着世俗的困惑、现实的羁绊,如张爱玲所言“咬噬性”的苦恼。
近日,在北京三联生活书店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刘剑梅与作家阎连科、梁鸿就共同探讨“女性精神独立”这一话题。
“这是一本男性看了会刺痛的书,它会让你正视自己在生活中是否真正尊重身边的妻子、母亲等女性”,阎连科接连抛出反思,“为什么中国的男性作家不能清晰得认识到笔下人物的性别?为什么他们笔下的女性永远是男性的附庸,永远处于被动的位置。我们应该检讨自己的角色,检讨自己的文学了。”梁鸿对此亦有同感,她认为很多作品中男性作家把女性描绘很美很纯,但这并未提升女性的心灵和形象,而是把女性简单物化。
对于女性在这个社会“精神独立”的艰难,刘剑梅深有感慨,《彷徨的娜拉》更是收录了她对贾平凹小说《带灯》呈现的“男权主义倾向”的批评,她直言“读后真的感到绝望,为优秀女性心灵远处存放而绝望,为千百年来的男性崇拜传统如此根深蒂固而绝望”,在《带灯》描述的男权乌托邦里,想改变现实世界的女英雄只能是男性门后桌前的“小猫、小狗”,再有本事也跳不出男权的五指山。
阎连科认为这其实是“文学性大于女性”还是“女性大于文学性”的问题,但根本的原因是“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在文学中谈论男性、女性是不予考虑的,而中国的大部分作家还没能跳脱出‘生存问题’的写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