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命运的人生》作者凯尔泰斯·伊姆雷说,“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使仇恨永远存在下去。”皮埃尔·勒努阿尔在《带条纹的地狱囚服》中写道,“我还属于集中营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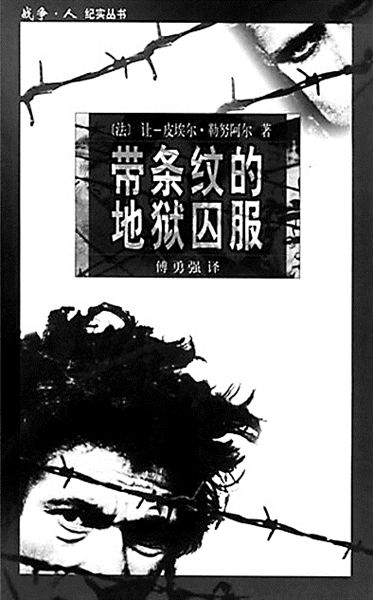
《带条纹的地狱囚服》 (法)让-皮埃尔·勒努阿尔译者:傅勇强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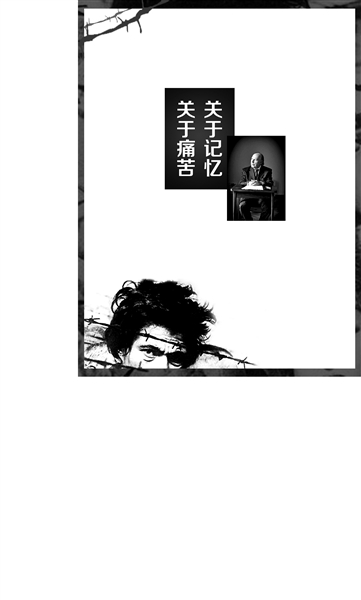
诺奖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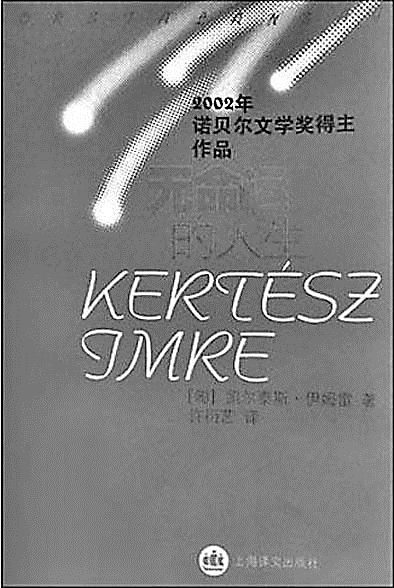
《无命运的人生》 作者:(匈)凯尔泰斯·伊姆雷译者: 许衍艺上海译文出版社
有许多历史的黑暗复杂地带,其实在我们理解之外。或者说,尽管有诸多文本在帮我们理解,但在当事人看来,仍然触不可及。我在这里缩小范围,说说奥斯维辛,以及两个亲历人的文本留给我的感受。
“我感觉自己与他们不同,完全是陌生人。我还属于集中营的世界。”一位名叫让—皮埃尔·勒努阿尔的法国老人这样写道。他的《带条纹的地狱囚服》这本回忆录最近我再次拿起,完全是凯尔泰斯的缘故,我读他的《船夫日记》读得入味,忍不住想将作家其他著作也拿来读。只找到上译版那本《无命运的人生》,旁边挨着的就是这本。都是几年前的旧书了,书脊还很细薄,若不是这样定向地翻找,看到它们也非易事。但是,该看见的,总会被看见。这只是个机遇与时间的问题。同样,愿意理解与能理解,这也是个时间的问题。
《无命运的人生》(另一个版本译作《命运无常》),也是带自传色彩的集中营文本,正好可以对比来读。他们一个是生于1922年的匈牙利犹太人,15岁被辗转运送至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等几个集中营;一个是生于1929年的法国犹太人,呆过几个集中营直至二战胜利。凯尔泰斯的书里,有大量的心理描述,仿佛一个内在的眼,在展开对环境、对人以及自己内心细致的探寻,阅读的进程也便如探寻本身一样难熬、不确定而且莫测。相比之下,让—皮埃尔·勒努阿尔的叙述要明快跳脱得多。片断式、跳跃式的场景捕捉,省略了很多前铺后陈。诸多形形色色的“人”,构建出属于集中营的特殊生态。“这里也是欧洲。”作者以希腊神话作喻,他说这里既有诸神(党卫军)、半神(替纳粹看管集中营的老德国犯人)、还有来自德国统治下不同欧洲国家的贱民。贱民虽然是命运的共同体,但也不意味着没有摩擦,相反,有时的对话还挺生猛:
“俄国同志,我的勺在哪儿?”“我他妈不知道。”“刚才还在桌上。”“我他妈没看见。”“我们彼此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说话,你没偷我的勺?”“法国傻X,叫唤什么。你要勺,这儿有。”他把我的弯勺扔在桌上,说。“法国傻X,你在这待得有日子了,早该晓得东西谁捡就归谁。”……
抄录出这一小段,因为它非常代表这本书的叙述风格。简洁利索,声画兼具,但没有别的。我却记住了这把勺子。我们通过电影建立起来的集中营想象,解放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了百了的解放,但事实远非这样:“很久以后听人讲,遣返的苏联人回去后全被处决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了。而其中一些人曾经有过英雄壮举,尤其是那些游击队员,他们在德国战线后方采取过有效的战争行动。但红军中所有军官或士兵一旦被敌人俘虏,就被称作叛徒,也被当作叛徒对待……”我猜作者写至此地,一定会联想到那把勺子。
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却是以平静与超然的笔触写下,这既令人震撼,同时也耐人寻味。为什么不将所受的苦难转成愤怒的挞伐,作者在后记中这样表达:“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使仇恨永远存在下去。”
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这本书最后一章叫《后遗症》,讲的是集中营生活对其后来生活的影响。与《无命运的人生》的最后一章异曲同工,他们都说到了一个感受:孤立与隔膜。经此一遭的人们,是否能够遗忘,以开始新的生活?凯尔泰斯笔下这位少年的回答是:NO。“发生过的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我终归不能够命令自己的记忆把它们给忘了的。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时,要么就是在我的大脑出问题或患病时,新生活才可能开始。”有过与旧时邻居不欢而散的对话,少年突然感到:“在那些烟囱旁边,在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而让—皮埃尔·勒努阿尔也遭遇过不理解,一次还是在他对奥地利犹太人说过一番话之后:“亲爱的,假如我不是法国青年,是德国青年,我也会参加战争,我宁愿不去思考让我执行的命令。”对方不解:“您受尽了所有这些痛苦之后,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是啊,怎么能?怎么会?但我知道语言有时的吊诡,让在这里用了宁愿与假如。正是这两个词,垫出了黑暗与苦痛的全部重量。
与凯尔泰斯的诺奖名声相比,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听来相对陌生,百度上的中文资料,还停留在与书相关的部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只是看到印在封底的他的肖像,依然精神矍铄、气色很好。此书是他晚年应孩子的要求所写,后记中他真心希望他所经历的是所谓文明国家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一位对世界心怀希望的老人,总是让人温暖,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说苦难会转化为人生的财富,这是一句笼统的话。苦难怎样化为财富,凯尔泰斯与这位老人,都提示了各自的方向。看《船夫日记》当知,《无命运的人生》只是凯尔泰斯思考奥斯维辛的第一步。他后来移居柏林,说要把大屠杀作为思考的起点。“现在,唯一值得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从这里继续前进?”而让—皮埃尔·勒努阿尔战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书中记录了与一位美国人的相遇。他告诉他,当年执行轰炸任务,目标正是他所在的米斯堡集中营。“后来我们常在一起打高尔夫球。没有怨恨。”这件事就此结尾。
朴素而高贵,是作家莫里斯·德吕翁对他这本书最精准的评价,但我体会到,这绝不仅仅指文体的质地,还指的是以这种文字来叙述苦难的那个人。
“我们和他们存在鸿沟。”莫里斯·德吕翁的推荐序里还提到一个关键词,要理解它就得同时理解凯尔泰斯这句话:“怎样才能处理好资料与整理原则之间难以跨越的断崖?如何避开那些经过修饰、反复出现的狡黠窥望的剧情?”创作者的自问,也差不多提示了作为观看者的我们所容易陷入的陷阱。而要弥合这断崖与鸿沟,就得如凯尔泰斯书中少年所说:“得把所有这四年、六年或者十二年都乘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二十四小时……最后再把所有这些都倒回去,每秒钟、每分钟、每小时,每天地倒回去,然后把所有的时间全都消磨掉。”显然我们没法做到,就像我们没法想象,在这消磨的过程中,除开那巨大的恐惧与颤栗,还有冗长的麻木与无聊。以及在我们听来颇不可思议的“幸福”。
而这两本小书,都在以各自方式提示着这些,可贵的还有,在深感不被理解中,他们仍自觉地搭建着这一记忆遗产与现实、未来之间的桥梁。(孙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