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文汇出版社推出文学“灯塔系”,第一辑精选两种:广东青年作家马拉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山西青年作家孙频的小说集《同体》。丛书名之所以为“灯塔系”,是要力图在当下纷杂的文学版图中,为读者指引一些值得信任的阅读方向,比如既关注文学新风,又关切现实深度。
马拉在国内多家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系70后实力派作家。《未完成的肖像》是马拉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书,极具叙事魅力,不动声色地表现艺术家的好奇,各种意想不到的境遇。马拉在后记中自白:“这种好奇让人绝望,你永远无法看到你不在现场的那一面,再强劲的想象也无法突破这坚硬的现实。”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未完成的肖像》通过书写一个艺术家群落的生活,揭示了现代艺术的进步主义、激进化、媚俗等诸多法则,对人之内在存在有深入的追问和细微的展现。”
《同体》则是80后女作家孙频的几篇最生猛酷烈的小说合集。近年来,孙频的一系列生猛酷烈的小说,受到了文学界很大关注。孙频解释,所谓“生猛酷烈”,“并不是篇篇都在写杀人放火,也不是可以用一句简单的不够温暖来概括。毫无疑问,我不属于腻歪婉约的写作气质,写上十年也未必能写出一点雨打芭蕉的风韵,写不出来我也不打算装。自认为更崇尚有力量的写作”。《同体》里的这几部中篇,都将人放置在极端的环境中去考量,活生生地“逼”出了一个个弱小个体潜藏的巨大力量。著名作家韩少功评价她:“对人性的独到侦测,对经验的鲜活释放,对语言的精准控制,使孙频在文学上高开高走。我既惊讶又好奇:她将要写到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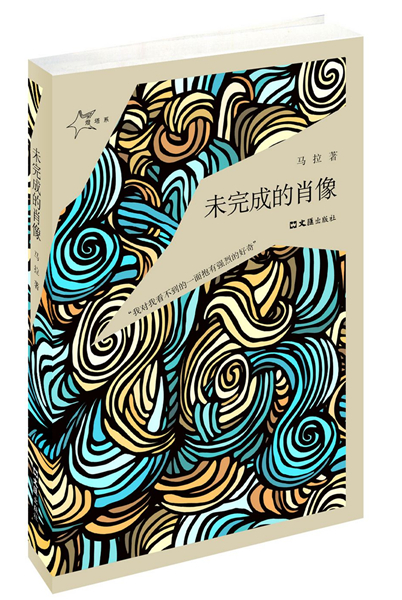
书名: 《未完成的肖像》
作者:马拉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定价:29元
【媒体推荐】
《未完成的肖像》通过书写一个艺术家群落的生活,揭示了现代艺术的进步主义、激进化、媚俗等诸多法则,对人之内在存在有深入的追问和细微的展现。
——谢有顺(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
马拉所采用的的语体,似乎是在向30多年前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这一脉遭到文学新人刻意遗忘的当代传统致敬,但它折射出的是比魔幻、寻根或是先锋更加尖锐的现实之恸。
——胡续东(诗人、批评家、北京大学副教授)
有人说马拉的作品有先锋意识,相对于传统的故事结构和叙述方式来说,我很同意这种评说。但是我更注意的是他的平静,是那种不动声色的陈述。我觉得,如果没有淡定的人生态度、人生立场,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学风格。
——徐南铁(评论家、文化学者、广东省文联副主席)
他让小说重新回到了想象的艺术世界中来,不再为被动地照搬现实的生活而困惑,从而在扩大想象力的视野上让小说重新回归到了开阔的人性领域。
——刘波(批评家、三峡大学副教授)
【内容梗概】
马拉在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后记中自白:“我对我看不到的一面抱有强烈的好奇。这种好奇让人绝望,你永远无法看到你不在现场的那一面,再强劲的想象也无法突破这坚硬的现实。它是神秘的,属于别人的部分。即使我是她的丈夫,她的父亲,也无法占有。”
【作者简介】
马拉,1978年生。诗人,小说家,中国作协会员,虚度光阴文化品牌联合创始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金芝》《东柯三录》,诗集《安静的先生》。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孙中山文化艺术奖,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红豆 超人杯”长篇小说奖。
【内文试读】
跟王树交往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王树其实是一个外表冷漠,内心狂热的人。他从民间艺术社辞职之后,一直躲在家里画画。和我不一样,他有个当教授的老子,懂得欣赏艺术,也愿意让他躲在家里画画。更重要的是他老婆也支持他画画,好像大家都觉得他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一样。
他老婆是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据说还是医院的骨干医生。我认识王树那么长时间,大概见过他老婆三次还是四次。她总是值班,带学生,做课题,医生的生活规律得有些枯燥。那是一个清秀的女人,笑起来嘴角还有淡淡的酒窝,脖子高出衣领一截,头发顺而且直。那会,我非常羡慕王树,觉得全世界的好事都让他占尽了。想辞职就辞职,想画画就画画,还有个这么好的老婆。我没想到的是,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表象,事实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他老婆的死近乎惨烈,《黄城日报》上还报道过。直到今天,我都想象不出来她是怎么死的,根据尸体解剖结论,她是活活饿死的。一想到这个,我就毛骨悚然,在这个伸手就能拿到东西吃的时代,一个人能把自己活活饿死,那多难啊。
出事那会,王树出去写生,他经常出去写生,少则一两个礼拜,多则个把月。王树回来打开门时,屋里的惨状把王树吓疯了。
一进门,王树闻到了浓烈的臭气,他还以为是下水道堵了,但洗手间里一切正常。他推开房间的门,一股巨大的臭气熏得王树几乎要吐出来。他看见他三岁的儿子躺在妻子的怀里,嘴唇干枯,听到门打开的声音,他的眼睛微微张开,嘴巴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妻子已经死了,尸体开始渗水。王树的脑袋一下子爆了。后来,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王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情处理完后,王树看到房间的门板后有淡淡的抓痕,那是儿子抓的,送到医院时他的指甲已经裂了,指甲缝里都是褐色的木屑。妻子死得很干净,表情镇静,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书,她似乎什么都不想说。
据医院的同事说,妻子一共只请了四天假。请假时,她的脸色已经不对了,但谁也没有往坏处想,都以为她是身体实在不舒服了。王树的父亲告诉王树,妻子来接儿子是王树回来前三天。也就是说,妻子其实是有预谋的。如果不是王树及时回来,儿子也有可能和她一起活活饿死。医学报告说,正常人如果不吃饭一周左右就会饿死,如果不喝水,三天左右就会死。从这个报告推理,王树的妻子带儿子回家之前大概有四五天没有吃饭了,接下来几天,她水米不进。
我听说过各种各样自杀的,也见过那些一心想死的人从十八楼跳下来。但像王树妻子那样活活饿死的,我是真没听说过。不知道她那瘦瘦的身体里藏着多大的怨恨和坚决的意志,她虐杀了自己。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树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他经常出现幻觉,一回到家,他总是看见妻子躺在床上,身体往下滴水。他不敢回家。后来,他干脆把房子卖了。我让他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他拒绝了。他说想一个人找个地方住。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让王树从痛苦中走出来。那段时间,我经常陪着王树,两个人很少说话,就静静地坐着。我倒想王树能大哭一场,大哭一场之后人可能就舒服了,像他那样闷着,我总担心有一天会出事。
打破沉默是在两个月后。王树找到我那儿,他一进门就说,老那,你陪我喝酒吧。我赶紧说,好,好,你等等。我出门买了一箱啤酒。回来时,王树已经把桌子摆好了。
喝了几瓶后,王树看着我说,老那,我不明白。
我说,怎么了?
王树说,她为什么要死呢?
我说,人总有想不开的时候。
王树说,她这种死法我受不了。
我说,算了,都过去了。
王树说,我过不去,我真的过不去,她这样死好像是死给我看的。
我说,你想多了。
王树说,我没想多。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经过那天晚上,我才真正了解了王树一些。王树的生活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他的妻子算是个好女人,至少外表看起来如此。她是医生,应该说她更懂得身体的结构和功能,但思想上,她并不比普通人看得更透彻。她总是怀疑王树在外面有女人。王树说,我怎么都不能说服她,也不能让她相信我。妻子心态好的时候,她也知道她的怀疑一点依据也没有,但她总是怀疑。甚至,她对王树说,她们家族有自杀的传统。她的叔叔是个少年天才,多次考上清华,但家庭出身让他上不了大学。他死于毒药。她的奶奶在爷爷去台湾后,跳水自杀。她说,她身上可能有家族的阴影。
和妻子的性生活也是不协调的。妻子有洁癖,连精神上都是。王树和妻子的性生活很少,一年大概不到十次。王树说,老那,你能想象那日子怎么过吗?我摇头。王树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的,但我真的没有找过女人,连小姐都没找过。我说我知道。
和妻子过性生活,对王树来说,如果不是实在受不了,他宁愿手淫。每次过性生活,王树都要提前告诉妻子,像打报告一样。妻子同意了,他们才有性交的可能。做爱之前,妻子会帮王树仔细地清洗身体,好像王树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她洗得非常细心,肥皂擦过王树的每一寸肌肤。妻子的手光滑,柔软,王树的阴茎挺立着,但不能有任何作为。洗澡时,妻子是不会和他做爱的。洗完了,妻子开始给自己洗。王树要在床上等半个小时,妻子才会从卫生间出来。做爱的过程也是相似的,妻子躺在下面,一动不动。刚结婚那会,王树试图将手指插入妻子的阴道,他想知道妻子湿了没有。妻子坚决地拒绝了他,妻子说,不卫生。王树亲妻子的身体不能超过腹部,超过腹部,妻子会及时地将王树拉上来。和妻子结婚六年,王树不知道妻子阴部的形状,每次他试图看看,妻子都会拒绝他,或者紧紧夹着双腿。王树说,我们是夫妻,我看看没关系的。妻子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她说,不行,你不能侵犯我的隐私。王树哭笑不得,他很想对妻子说,那我和你做爱算什么呢?那话他不能说,说出来后果会很严重。妻子当然从来没有给王树口交过,她说那是对她人格的侮辱。王树怀疑妻子是性冷淡,性对她来说,是付出,没有一点享受的意思。除开准备怀孕那段时间,王树每次和妻子做爱都是戴套的,即使在妻子上环之后。王树说,我和她结婚六年,真正进入她身体的次数应该没有超过十次。他说,也许从一开始,妻子就不应该和他结婚,她可以找一个和她同类的男人。
王树是个艺术家,在妻子的理解中,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放荡的。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妻子嫁给王树却又是坚决的,她把自己当成了祭品。嫁给王树之后,她仍然没有意识到她和别的女人的不同,她一直以为王树的性欲和他艺术家的身份有关。她不能满足王树,这一点,她后来知道了。知道之后,她开始担心,并且产生幻觉,认为王树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到后来,她的幻觉慢慢加重。她说,王树,我看到你和别的女人上床了。妻子像狗一样嗅着被子和枕头说,这里有女人的味道了。妻子说,王树,我是不会离婚的,我就是死了我也不离婚。王树说,我没想和你离婚,我也没别的女人。妻子说,算了,你别骗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有女人了。
因为这些幻觉,妻子越来越瘦,尽管外人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甚至说她的身材越来越好了。终于有一天,妻子对王树说,王树,我知道你现在害我的心都有了。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我会让你知道我不会粘着你不放。妻子的话,王树不喜欢。他说,你胡说什么啊。这样过了大半年后,王树对妻子说,我出去写生。妻子笑了笑说,你终于还是要走了。王树说,我不是要走,我是出去写生。妻子说,你不会回来的,你会后悔的。
现在想起来,王树觉得妻子的种种行为已经给了他很多暗示。妻子本来可以不用死的。他说,老那,我觉得她的死和我是有关的,她那样死是为了惩罚我,让我一辈子不心安,她赢了。
我说,王树,其实没什么的。过几年,你说不定就把她忘了。年年都死人,我们哪里记得了那么多。
王树说,她不一样。
我说,王树,不管怎么着,反正人都死了,活着就得往前看。
过了一会,我对王树说,你找个女人搞搞,可能什么事都没了。
王树说,是吗?
我们俩把一箱啤酒喝完后。我说,王树,我们别在家里喝了,出去喝吧。王树点了点头。
酒吧还没关门,十二点,时间还早。我们在酒吧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出来时,我们带了两个女孩,大概不超过二十岁,戴着夸张的耳环。小美和小丽,我认识她们挺长时间了。她们都在酒吧做啤酒妹,偶尔也和熟悉的客人出台。我站在酒吧门口对王树说,去我那儿吧?王树说,好。

书名: 《同体》
作者:孙频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定价:30元
【媒体推荐】
对人性的独到侦测,对经验的鲜活释放,对语言的精准控制,使孙频在文学上高开高走。我既惊讶又好奇:她将要写到哪里去?
——韩少功(小说家)
孙频的写作从容大气,在新一代的作家群中,她早已脱颖而出。
——苏童(小说家)
孙频对她所写的人物一点也不隔膜,所以她在小说中所传达出来的情感特别真切。尊严似乎是孙频在小说中反复表现的主题。我觉得这很好,一个作家如果将一个伟大的词语反复表现,将其表现得非常充分,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去展示它。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呀。
——贺绍俊(评论家)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在《同体》等作品中,孙频更为猛烈地撕裂着她的人物,并不怜惜这些人物的内心早已长满荒凉的尖刺,撕裂之酷烈,甚至于带着一种黑暗的快感。从八十年代中期王朔的作品开始,青年男女们就以堕落为名,承担着彼此内心的绝望。所有的故事总要重复两次,只是火焰这次不再被海水所熄灭,火焰鲜红剔透,凝聚为黑夜中血色的琥珀。
——黄平(评论家)
【内容梗概】
作者在后记中自白:“《同体》应该是对我几篇最生猛酷烈的小说的合集。所谓生猛酷烈,并不是篇篇都在写杀人放火,也不是可以用一句简单的不够温暖来概括。毫无疑问,我不属于腻歪婉约的写作气质,写上十年也未必能写出一点雨打芭蕉的风韵,写不出来我也不打算装。自认为更崇尚有力量的写作。”
【作者简介】
孙频,女,1983年生。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太原文学院。出版有小说集《隐形的女人》《三人成宴》等。曾获十五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第五届北京文学奖,2009-2013赵树理文学奖,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
【目录】
同体/1
月亮之血/55
菩提阱/115
乩身/167
后记/214
【内文试读】
“其实你想,怎么活还不就那几十年,横竖是要死的。阳光好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边傻笑边想,能把这么多年活下来真他妈不容易。一眼看到底了,这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做什么工作你还能不和男人打交道了?就算你嫁个有钱男人,那本质上也不过是在搞批发卖淫,做小姐只不过和男人打交道更直接些罢了。”
昨晚,曾在一条流水线上做过活的工友给冯一灯介绍工作,结果介绍到了一家按摩院。工友如今是专业掮客,说服起人来那也是专业水准,她慈悲地看着冯一灯说,你如果不想再去流水线上做工,想来钱快一点活一点,就只能做这个。要知道,就连那些读完大学的孩子们也像满街的石子一样被踢来踢去,根本不值钱。
话虽如此,冯一灯还是没敢进去,站在门口瞻仰着灯光里的按摩院,玻璃门后是黑夜的芯子里孵化出来的一团桃红色,像是没有蜕化完全的白蛇还留着尾巴一般,那滞暖妖冶的桃色里有一种比黑夜更深的东西正像血液一样在缓缓流动着。
那桃色溅到了冯一灯的手背上胳膊上,像一种藤萝植物正要从那肉里长出来,殷实,茂密,邪恶。她有些不寒而栗,忙往后退了一步。桃红色的灯光里摇曳出了三个年轻女人的影子,边缘清晰却面孔模糊,像三只卡在琥珀里的虫子,永世不得出来了。她们穿得极少,两只热气腾腾的乳房好像随时要从衣服下面跳出来,简直是欢呼雀跃。脚上踩着的两只松糕鞋像小板凳似的把姑娘们的大腿高高供起来,姑娘们往沙发上一坐,六条明晃晃的大腿越发像橱窗后面的商品,直往人眼睛里逼。
冯一灯觉得自己像个即将被绑上刑场的囚徒,似乎再往前走一步就要被装进去封口了。她虚弱极了恐惧极了,转身欲逃。工友连拉带扯地拖住她,让她进去体验一下再说,冯一灯毕竟是她到口的一块肉,怎么能让肉自己跑了。
最后冯一灯还是落荒而逃。自打离开水暖村,这也不是第一次被撺掇着去做小姐了,似乎只有做了小姐打工妹们才是取到了真经。可是她不能,她觉得要是真做了这个就永世不用想再见父亲了,他一定不认她了。可是她还想见到他,她一天天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一天还能回到他身边。她欠他一句话。爸爸,对不起。这句话她已经欠了他七年。
钻到地下室睡了一夜之后,又要被迫开始新的一天,她忍不住想起了昨晚工友说过的话,想要来钱快一点就只能做这个了。是啊,一个高中都没读完的女孩子还能做什么?她刚从工厂辞职出来就不小心混到了传销的队伍里,被困了两个月才伺机逃出来。现在混到这个城市已经快半个月了,找不到工作,身上那点钱一天天在蒸发。每一天都像是从同一个模型里拓出来的,每一天都一模一样,她像被铸死在里面了,连条爬出去的缝隙都找不到。
晃荡一天,黄昏接踵而至,冯一灯惧怕接下来的天黑。天一黑下来,那地下室就像大地上裂开的一道口子把她吸进去,她无处可逃。在黄昏的光线里,她沿着河边的甬道慢慢往前走,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这座城市的春天迎面而来,碰到她的脸又分开,从她的两侧悄悄向后伸去。路两边的柳树刚刚长出鹅黄色的眉眼,这许许多多的眉眼挤在一起,如烟似雾,她从这发丝一般的柳枝下穿过的时候,竟像是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过,到处是眼睛,到处是人面,反而让她愈发凄凉。这个偌大的城市里至今没有一个地方肯收留她。
路边坐着一个年老的乞丐,是个瘸子。他睁着两只木质的眼睛一下一下呆滞地看着她,那目光落到人身上有一种迟钝的痛,挨了木棍一般。他的一只手空空地机械地敲着手里的塑料碗。他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便从钱包里取出一张十元的钞票放进他的碗里,这意味着她今晚不能吃晚饭了。老乞丐嘴唇抖动了几下,但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只是看着她。她突然生出了对这老乞丐的眷恋,她在他面前蹲下。在这个忧伤的黄昏,她想从他这里索取一点点慈祥,这种渴望太剧烈了,几乎让她泪下。她想他能和自己说几句话,此刻她想有一个老人随便和她说几句什么。她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吗?老乞丐只是摇头,嘴唇无声地抖动着。他像个老婴儿,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无法施舍给她。末了,他又敲起他那只空空的碗,像只上了发条的闹钟,把这黄昏的光线一寸一寸地敲碎了。
连乞丐都不会施舍她。她绝望地站起身,继续往前走。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夜色里的柳树忽然变得有些鬼影幢幢,身后乞丐的敲碗声在夜色里戛然止住了。冯一灯莫名地打了个寒战,她不敢回头却清晰地嗅到了黑暗中似乎有一双眼睛正看着她。她加快脚步仓惶地往前走,脚上的高跟鞋敲着石板,破碎,寂寥。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摩托车的马达声袭来,身边的柳树在车灯光里溅出了比白天还要明亮鲜艳的绿色,绿得让人毛骨悚然,她的影子被灯光扣在地上,巨大松散却动弹不得。她向身边最近的一棵柳树扑去,一辆摩托车从她身边擦过去的一瞬间,一只手从车上伸出来拽住了她的手提包。
此时,手提包的带子还被她牢牢攥在手里,在摩托车飞出去的一瞬间,她整个人随着手提包也一起飞了出去。这带子对她来说如同脐带,脐带连着的那只包里装着的是她可怜的全部家当。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像架巨大的飞机一样盘旋着,她仅有的一点钱全在这包里了,这只包没有了,她就身无分文了,这念头像螺旋桨搅起的离心力要把她整个人都吸进去绞成齑粉。她像只蚂蟥一样死死叮在那条带子上,摩托车拖着她一路狂奔,她眼睛里什么都看不见,却能在黑暗中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肉身与石板和金属撞击的声音,就像两件冷兵器撞击的声音,回荡在浩大的夜空之下。事实上,她已经感觉不到自己肉身的存在了,包括肉身上所有的疼痛都被这个铁一般坚硬的念头给腐蚀掉了。
她就那么被焊在一条皮带上被拖着走了一段路,摩托车突然加大油门向右侧拐去,同时把她狠狠撞在了路边的一棵柳树上。
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样一个晚上居然还有月光。就像在血腥的油画底色上涂了一层柔软的光晕,下面却仍然是寒光凛冽的血色。一缕意识慢慢苏醒过来了,像蛇一样咬着她,现在她真的身无分文了。再接着,就连这缕稀薄的意识也慢慢从她身体里流走了,她周身变得又薄又脆,像一只四处走风漏气的容器,所有的思维、血液都流走了。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周围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声。只有一两尾鱼的尾巴从河面上倏然滑过,溅起了微弱的水花。
一抹残月正挂在夜空,月是下弦。
有液体从额头上流下来糊住了她的眼睛,她知道肯定不是泪,她的眼珠子此刻干得像块炭火,连一丝潮气都泛不起。她没力气去擦,血液便慢慢把她的两只眼睛淹没了,她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她听到了,下意识地动了动,但起不来,好像四肢都被临时拆卸掉了,七零八落的一地,却都不是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听出来了,这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这是一堆诡异的脚步声,像突然在黑暗中蔓延出来的血红的石楠花,已经盛开在她的脚下了。近了,近了,更近了,忽然之间,脚步声在她身边戛然而止,像鼓点一般齐齐踩着她的神经停下了。
她在惊惧了一秒钟之后,开始像尾上岸的鱼一样挣扎起来,她昂起头瞪着两只被血糊得模糊不清的眼睛试图往前爬。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巨大冰凉的手——她在很久之后都一直记得这只手的温度——牢牢钳住了她的胳膊。
脸上的血迹开始发干,像水泥一样把她的眼睛砌了进去,她用尽力气也看不清眼前是个什么人,只感到他那一双无处不在的冰凉的大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