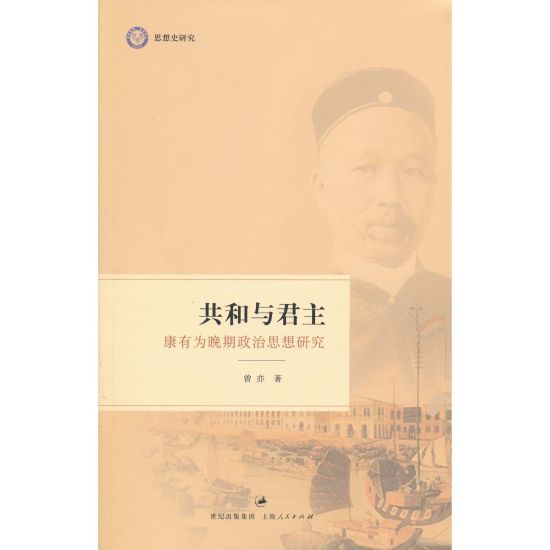
《共和与君主》
导语
曾亦此书之所以堪称纯正的保守主义,恰在此处。作者没有扭捏作态以迎合学界似是而非的政治正确,也没有回避实质的价值层面的冲突,相反,此书行文中随处可见立场鲜明、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批评与反诘,读来或令早已习惯于现代立场的读者每觉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作者简介
韩潮,青年学者。
辛亥百年之前,坊间得见曾亦先生论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的新书《共和与君主》,实是一大幸事。
就我目力所见,曾亦此书或者是百年来最为纯正的保守主义论著之一。保守一词,辛亥以来大体是不名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外中国学界发动的激进保守之辩,虽然多少恢复了保守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声誉,但在我看来,其中多少还有狡黠暧昧的成分。比如,海外知识界的激进主义批判其主导性议题是五四运动,而不是辛亥革命。这种保守主义的论调,其策略是很明显的,说来无非是两条:一为舍政治而守文化,一为舍辛亥而攻五四。但如若一面撇开辛亥年的革命不论,另一面撇开保守主义应有的政治内涵不谈,这种保守主义,恐怕是太轻巧了些。
说来,保守主义本是现代世界的异端,是附着于其背上的牛虻。保守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从来也就背负着污名,譬如过去常有反动一词,形容其人其学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倘若果然面对潮流迎逆之情势,那么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必当逆流而行,又岂可因一时之污名而放弃从来信靠的原则——道不同则不相与谋,彼之反动,我之孤往,如是而已。
曾亦此书之所以堪称纯正的保守主义,恰在此处。作者没有扭捏作态以迎合学界似是而非的政治正确,也没有回避实质的价值层面的冲突,相反,此书行文中随处可见立场鲜明、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批评与反诘,读来或令早已习惯于现代立场的读者每觉芒刺在背、坐立不安。辛亥百年以来,保守主义偏居一隅,气息若断若续,早无酣畅淋漓、元气充沛的文字,今日得见曾君罕见的“战斗式的保守主义”,不由得感叹:辛亥百年,终于得见,保守者归来。
二
初看上去,曾亦先生此书主题似乎仅限于讨论康有为晚期的政治思想,但实则作者念兹在兹的是中国传统与辛亥年革命之间的碰撞。作者以《共和与君主》为名,其实并非专论康有为政治思想中的政体学说——实际上,书中专以君主制与共和制比照立论的章节不过数页,我私下揣度,作者嘱意的当是辛亥年的界限和殊途:首先,就历史断代而言,一边是辛亥之前三千年君主制的古代中国,一边是辛亥后百年共和制的实践。其次,辛亥革命也标志着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努力的失败。辛亥一役,最大失败者不是清政权,而是康有为等君主立宪派。戊戌到辛亥之间,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曾有一场绵延十数年的政治论争,这场论争是晚清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论争,或者也是古代中国最后的政治争论。然而,所有这一切未及澄清分明即在辛亥的隆隆炮声中嘎然而止。
辛亥之前,康有为虽流亡海外,但他一手建立的保皇会(后改称国民宪政会)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力或者还要超过孙中山的兴中会,更为重要的是,清政权一日不亡,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争论一日不休,康有为的立宪立场一日就不失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然而,辛亥之后,革命的车轮滚动起来,历史已全然走向了康有为的反面。康有为倡君宪,历史走向的是共和;康有为倡渐进,历史走向的是急进;康有为主“志在大同,事在小康”,历史走向的是大同世界再造人间。就历史的逻辑而论,康南海当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者。
不过,曾亦先生此书遵循却是并非此种历史的逻辑,相反,作者颇有些为失败者立言的意味。作者把康有为晚期定为辛亥之后,此说与常见把康有为后期思想定为戊戌之后,多有不同,但这恰也是此书立论的根本。作者开篇首章以“共和后中国之怪现状”为题,实则引出的问题是康有为对辛亥革命以及对革命后之共和乱象的批评和反思。这与通常所谓康有为戊戌后从最为革新的改革派转变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派的判断显然旨趣大异。一攻一守,其中意味,自不待言。
三
西方保守主义始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柏克、迈斯特以下皆然。而此书首章的意旨实有类似的意趣。在我看来,作者似乎挑起了一场从保守主义立场重审辛亥革命的论争。从表面上看,革命派是成功者,立宪派是失败者,但革命非但没有解决保守主义立宪派的疑难,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保守主义对革命共和对现代性的反思,这就是首章名之为“共和后中国之怪现状”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论,康有为的晚期思想难道不应称作现代中国的“辛亥革命沉思录”?
民初乱象,本是一个昭然的事实。辛亥之后,康有为早有“呜呼噫嘻吾不幸而言中”之论,又自创《不忍杂志》,其发刊词谓“见诸法律之蹂躏,睹政党之争乱,慨国粹之丧失,而皆不能忍,此所以为不忍杂志”。而在1923年致吴佩孚的电报中康有为甚至有一句愤激之词,“十二年来号称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共杀,以召共管而已”。不过,此前的研究者多未能严肃对待康有为对民初社会政治乱象的批评,可能在他们眼中,无论是康有为“不幸而言中”的慨叹抑或是所谓“不忍”之辞大概都是政坛失意者的无谓呢喃罢了。再加上康有为对民国政治的不满,导致他参与了1917年张勋主导的复辟,于是乎“封建余孽”的帽子是彻底坐实了。
我不敢说此书作者是真正同情地了解康有为晚年焦虑所在的第一人,毕竟此前萧公权先生汪荣祖先生都为晚年康有为的思想做了较为充分的辩护,但如作者此书第一章分别以“政治之分裂”、“民生之凋敝”、“风俗之败坏”三个角度透视共和后中国的整体乱局,并名之为“共和后中国之怪现状”,或者才是真正站在康有为立场上的反省。作者借康氏反思所陈列的史实如民初的军费开支、外债水平、民生状况等等无不说明,若论社会总体的败坏程度,民初实则有甚于清末,而康有为对民初社会政治状况的焦虑绝非政坛失意者的无谓呢喃,相反是句句切实有所指。
我稍加补充的是,即便是康有为寄托过高实则无能为力的复辟经历,亦非全然无当之举。康有为本人一再声称,此举无非是效仿查理二世复辟克伦威尔共和国的经验,或者更有以光荣革命终结一切革命,也未可知。更何况,康有为对当时共和格局的不满并非出自个人的私怨——试举一例,张勋复辟之时,严复虽未参与其中,但却认为,“复辟通电,其历指共和流弊,乃人人之所欲言”。
事实上,民国初年共和之后,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思想史现象,就是老新党与新新党的分野、以及老新党们的集体后撤。落伍的康有为和严复自不待言,就是作为辛亥革命重要参与者之一的章太炎也在晚年回归他曾一度痛砥的本土传统,甚至欧游之后的梁启超对现代性的认知也复杂了许多。何以曾经的维新者、曾经的革命者、曾经的西学译介第一人在革命之后反倒集体性地后撤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