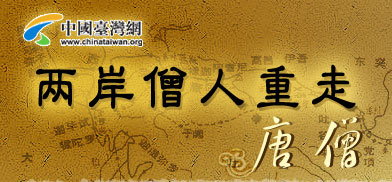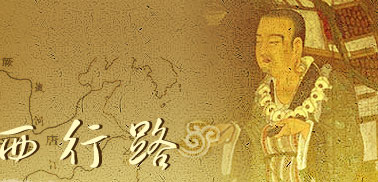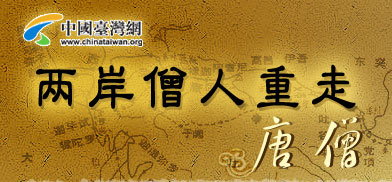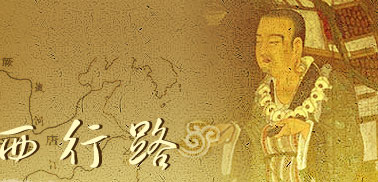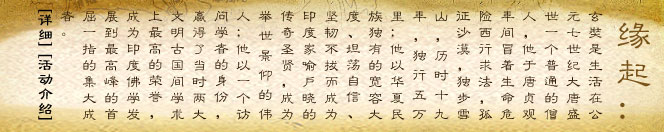一.终南山
常听人说起终南山,说某某曾在那里苦行过,话里流露出高山仰止般的敬重。是因为律宗祖庭净业寺在终南山上?我不敢肯定,不过,终南山在我心里已成了“苦行林”的代名词。车进山没多久就停了下来,卖票的姑娘在喊:到净业寺的下车。车上没人动,只有我下了车。我在路边恍惚了好一会,疑是那姑娘报错了站名?只见四周苍山呆立,不见寺宇,也不见亭台楼阁。没有一点旅游迹象。难怪乘客都不下车的,他们熟悉这里的山水,也知道卖票的姑娘经常报错地方。 太阳钻进云层里,眼前的山峦陡然失去了颜色,像是换了一个世界,我不熟悉这样的世界,我独个儿在路边彷徨。 我发觉路边有条石阶道,曲曲的,通向云端。我心头一喜,我找到了我要走的路。我一步一步往上登,回头看,石阶道上没有留下我的脚印,这无妨,我不在乎我身后留下什么,我只执着自己走过。
石阶路两边杂木丛生,林中偶有叽叽鸟鸣,使清寂的道路显得更加漫长幽深。我不敢将脚步放得太重,我疑惑着脚下的路是真实,还是虚拟?约莫走了一个钟头,见石阶道的一边有座古塔,隐约在树林里。走近古塔,往塔跟前一站,塔身比我高了一头,塔的正方刻有字,只是被风雨侵蚀了,漫灭得无法辨认,我不懂建筑,没法根据塔的造型去判定塔的年代。再往前走,转过一道山弯,迎面撞来一寺宇,傍山临崖,寺前有颗古树,老得只剩下躯干。树下有个和尚在打坐,我不敢弄出声来,轻轻地从他身边走过。来到寺前,寺墙上赫然跃出几个大字——律宗祖庭净业古寺。我到达了目的地,但我依旧分不清眼前的景物是幻影还是真实。
寺里没有游人,也不见僧人,显出几份诡秘与神异。殿堂门是开着的,我进去叩了头,我的心不知为何突然怦怦跳个不停,像快板的木鱼,我默念着“阿弥陀佛”想让自己静下来,可我把持不了自己。我没敢抬头,我说不出殿堂里供奉的是净宗开山祖师道宣律师,还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梆梆梆……一阵清脆的板声冲出寺门,在群峰之中回荡,像是在呼唤远方的梦人。这时,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殿门口有晃动的人影,是寺里的僧人,不知是从哪儿出来的,他们急匆匆地往斋堂里赶。我这时才觉得肚子在咕咕地叫,可我没敢跟着他们走进斋堂,虽说一个罗汉一份斋,可我还是拿不准里面究竟有没有我的饭菜。我从斋堂门前走过,走得极慢极慢,我盼着有人出来叫住我,问我为何不进去吃饭。可他们只顾埋头吃饭,谁都没有注意我,他们的世界里似乎只有他们自己。
我往寺后的山林走去,蛮失落的样子。 无意中我走到道宣律师“应供处”。 应供处在寺院后面的山崖上,崖谷深不见底,我是将身子贴在壁石上,一点一点地移过去的。应供处是张天然的石椅,端坐椅上,正念思维,满目苍翠,心旷神怡。 道宣律师当年在此苦修头陀行,终日宴坐崖前。他的苦行感动了天人,天人每日午时送来饭菜,以滋养他的色身。山下的人得知有个和尚在山中苦行感动了天人,于是,纷纷上山看个究竟,人们远远地望见一人影印在磐石上,八风吹来,人影如如不动,跟磐石一般坚实。大家身不由己地跪在地上潮着影像顶礼膜拜。苦行僧苦行的事儿越传越远,上山朝拜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有人提议在山中建一寺院,让苦行僧有个安身之处。这一提议即刻得到了众人的响应,没花多长时间,寺宇建成,取名净业寺。 这个故事遥远得有点不好思议,而道宣律师根据昙无德部(律分五部,昙无德部为五部之一)所开创的南山四分律宗,与相部宗(法励创)、东塔宗(怀素创)并称律宗三家却是真实不虚的,当时,三家并行,律法在东土空前地繁荣,而流传于后世的只有南山四分律。
二.华严寺
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除禅宗外,其余七宗的发祥地皆在西安。华严宗是佛门大宗,我一路打听其祖庭华严寺在哪儿,可连常住在西安的僧人都摇头,我买了本《西安名胜导游》,翻阅了好几遍,华严寺还是没个影儿。看来,我根性愚钝,无缘于圆顿大法。正在我心灰意冷时,却意外遇到一位老僧,他告诉我华严寺在城南三十公里的少陵原南畔,只是寺院已没,仅存两座塔。
按老僧指点的路线,我找到了华严寺双塔。 少陵原南畔半腰处有块平地,呈三角状,一角的外帮有堵石墙,双塔就矗立在石墙边。另一角有几间简陋的房舍,像是临时的工棚,墙体用黄土夯成,墙上有雨水冲刷的道道沟痕,房顶一半瓦一半草,黑白分明。走进房舍,见一人正埋头用毛笔在抄写着什么,见我进去,他吃了一惊,这里大概不是常有人光顾的,不然用,那人为何这般神情?我想给华严祖师叩个头,可我找不到祖师的身影,屋里空荡荡的,连个挂像都没有。我正迟疑,见那人放下手里的笔,慌慌到我跟前,倒头便拜,说给法师接驾,“接驾”两字的尾音拖得老长,跟唱戏似的。我赶忙还礼,礼毕,这时才看清他的模样,他岁数不大不小,跟我一般年纪,虽剃了个光头,可衣着一半僧一半俗,鞋子是纳底的,沾满了泥尘,朴实得像个农民,也像个苦行僧。他说他刚来这里住,这房子也不知是谁留下来的。我问他这里有香火吗?他说没有,附近的村民都不信佛,却偶有学者来搞研究。他问我是不是学者,我反问他我像学者吗?他笑了,他说不像,学者都喜欢戴着厚厚的眼镜,眼镜下面挂着张苦瓜脸。
我们有说有笑,跟老熟人似的。我说去看双塔,他说他陪我。我们一道向双塔走去,他边走边说:听老和尚讲,这里本来有许多树木的,原下也没村庄,更没公路。他朝原下的村庄看了看,接着说,这些房子都是后来盖起来的,人多了,原上的树木都被村民砍光了,寺院在一次大雨中随着塌方滑了下去,一个祖庭就这样被毁了。他声音突然哽咽悲怆,他哭着脸问我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我回答不了,我不敢看他,我把目光移向双塔。 东边一塔四面七级,是华严初祖杜顺禅师塔,唐贞观年间建;西边六面者为四祖清凉国师塔,建于元代,乾隆年间,原崩塔断,后在残塔上续建成五级。顺着双塔向原下看,见村庄中间有所小学,孩子们在操场上快活地跑着,他们一抬头就能看见原上又旧又破的双塔,他们会不会去问他们的老师,那原上的两个塔是从哪儿来的。
三.香积寺
去香积寺时,颇费周折,我在村落之间来回走,从中午走到下午发觉自己还在原处(那里的村子都是一般模样),万般无奈,只好叫了一辆小三轮。小三轮像条游鱼,在村间地头突突飞奔,不知穿过多少田舍,也不知最终到达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而香积寺就在那个村子里。 我找到了香积寺,却找不到进寺的门。 寺门在一蔽静处,门不宽,也不见门上有香积寺的字样。门是关着的,我敲了好半天,才听到里面有咳嗽的声音。门开了,开门的是位瘦弱的老僧,脸木木的,没有惊异,也没问我:你是谁。他不住地咳嗽,低着头,弓了腰背。我向老人合了掌,老人没理睬,他一边咳嗽一边关上了那扇与世相通的门。
我在寺里转了一圈,见到的都是年老体衰的僧人,他们或躺或坐,闭目念佛,有的在殿前走动,却举步维艰,步态蹒跚。寺里的建筑跟老人一样,沉沉的,没有生气。檐角下斜挂的太阳,也是昏昏的,与古寺及古寺里的人僧相映成“凄”。 天色已晚,我怕误了回西安的车,我转身欲离寺,走到一殿堂前,一老僧拦住我,叫我进去吃饭,我不想吃,却不由自主地跟了进去。老僧叫我自个儿盛饭,我拿了碗,却找不着饭,问老僧,老僧用筷子在我跟前的瓦盆沿上敲了敲,发出闷闷的声音。瓦盆陈旧得像件文物,里面的食物呈糊状,灰灰的,还伴着股酸味。我用勺子尖挑了点,勉强咽下,却直想吐。我怀疑那食物是前朝遗留下来的——一份让后人难以下咽,又不得不咽下去的苦涩。
四.青龙寺
青龙寺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 隋文帝举行完隆重的开国庆典,他紧接着想做的事就是修建城池、清整街衢,整个皇城在兵火交加中百废待兴。颓记的城池哪里留不住春日的温梦,城内城外的厮杀虽尘封史册,可文帝心里总有种无可名状的恐惶,那十万大军肉搏于城下的惨景,不能不让他惊悸。于是,他下令在城南乐游原上建一寺宇,超度死于兵难中的亡灵。寺成,取名灵感寺。看来,文帝的愿望还是相当善良的,他祈求佛菩萨的慈悲与灵感,化却兵劫中的冤怨,当然,自幼在寺院里生活了十三年之久的他,是有这份悲心的。
唐睿宗时,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是谁将灵感寺改为青龙寺。 8O4年,在一个洒满月色的夜里,咸阳古道上闪现出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借着溶溶的月光,不难看出是位僧人。他衣衫破褛,满面风尘,但稳健的脚步透露着力量和信心。他叫空海,是从东瀛岛国来的。 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天朝王国的从容与大度。 746年,空海随东瀛国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求学,因在海中遭遇风暴,同行者皆在风暴中遇难,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在海上飘泊了三十四天终于在福建登岸,后辗转到长安。
在长安期间,他遍游古寺,寻访名僧,贪婪地汲取天朝文明。 他当然要去朝拜青龙寺。 走进了青龙寺,走进了胎藏金刚界的大曼荼罗,只见檐角高啄,下映芙蓉之地,竹林果园,中秀菩提之树;此教所尊奉的大日如来及护法诸神在曼荼罗中各就其位,排列有序。他被眼前的庄严震慑住: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世界吗? 近来,日本真言宗多次到西安寻访开山祖师空海和尚的足迹,可青龙寺在北宋年间坍灭了。1979年,空海故乡香川县知事前川忠夫先生来西安访问,并提出要恢复青龙寺,就这样,湮灭千年古寺,终于重现人间。 我站在乐游原上,眼底的景物让人迷离——市井喧哗,尘土飞扬,而李白笔下的“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只能留给后人去感怀,去追忆了。
我往寺内走去,刚跨过门槛,一位穿工作制服的人拦住我,问我买门票没有。我说我是僧人,他说生人熟人都得凭票入寺。我只好退出,当然不会去买门票。沿着寺外的黄土路往前走,黄土路蜿蜒向前,不知伸向哪里,它能避开这喧嚣纷繁的世界?
(来源:《甘露》藏学)
编辑:蒲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