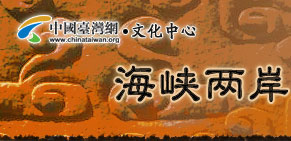道家与“神农”其人其事
——《庄子》、《淮南子》所描绘的“神农”形象
黄 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神农是传说中的人物,对于其人,不仅在我国儒家文献中有一系列相关记载,而且在道家文献以及其他史籍中亦有许多相应记载。这里拟以《庄子》和《淮南子》为例,说明道家笔下的神农形象。揣摩两书关于神农的描述,可知它们多是作者们虚构出来的,属于寓言性质的东西,旨在借圣贤立说。《庄子》所写的神农,表达了庄周学派的理想追求;《淮南子》所写的神农,则表达了秦汉新道家的理想追求。尽管如此,两书中有些记述,仍从特定角度保存了一些有关“神农”的传说性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神农 道家 《庄子》 《淮南子》
神农是传说中的人物,对于其人,不仅在我国儒家文献中有一系列相关记载,而且在道家文献以及其他史籍中亦有许多相应记载。这里拟从道家视角,并以《庄子》和《淮南子》为依据,简要谈谈神农其人其事。
一、关于神农其人
神农,又称神农氏,我国历史上的古帝之一,与燧人、伏牺并称“三皇”(据《尚书大传》说)。相传,“神农”生于姜水,以姜为姓。“起于烈山,又称烈山氏”,“初都陈,后迁鲁。立一百二十年而崩,葬于长沙。”(参见《辞海》,中华书局据1936年版复印本)
(一)神农与黄帝、炎帝的关系
神农乃轩辕黄帝之前的古帝,据《史纪·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不能伐。”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貊、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由此可知,神农氏乃是轩辕黄帝之前的一位天子,因后来权势衰颃,无力征讨“暴虐百姓”的诸侯,便被“修德振兵”的黄帝所取代。
神农,亦说即是炎帝。故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中有“以神农为赤帝”一语,“赤”与“炎”通,据此,则“神农”即“炎帝”也。但从司马迁的纪载来看,似乎炎帝与神农并非一人。读《史纪·五帝本纪》所载,可知在司马迁眼中,黄帝与神农的关系是“代”与“被代”的关系;而黄帝与炎帝的关系,乃是征讨与被征讨的关系,则神农与炎帝并非一人。以上两种见解,孰是孰非?目前因资料阙如,难以判断,姑且存疑,以待后来者新的发现。
(二)神农的历史贡献
神农作为一代古帝,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过卓越贡献。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神农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开创者。《周易·系辞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据此可知,神农发明了木制农具“耒耜”,给农业带来了“耒耨之利”;又《淮南子·齐俗训》载: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这一记述告诉我们,神农曾带头从事耕织,“以为天下先”。这对于“教民稼穑”,发展当时的农业生产,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二、神农是中国古代用中草药疗病的开创者。《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里不仅记载了神农“教民播种五谷”的历史功业,而且突出强调了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这是对古代用中草药治病即中医事业的确立所作的开创性贡献。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神农将自己的生命置之于不顾,乃致遭遇“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惊险历程。
其三、神农是中国古代商业的开创者。《周易·系辞传》又曰:神农之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里告诉我们,神农时代,在日中时分,举行集市交易,召致天下民众,汇聚天下货物,让百姓们相互交易,“各得其所”,满意而归。显然,这是对中国古代原始商业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以上,神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开创者、中医药的开创者以及古代商业的开创者,其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一切,神农受到华夏民族的拥护与崇敬是理所当然的。
二、道家所描绘的神农形象
道家是春秋末年的老聃所开创的以“道”为最高范畴的一个著名学派。这个学派为了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常借古代圣人之言行来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老子》一书,未列古代具体的圣人之名,但全书用“圣人”立说共29见。后来的道家学派,为了发展或推进老子的学说,往往将“圣人”具体化,对古代三皇五帝多有涉猎,亦反复提到“神农”其人其事。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笔下的“神农”,多属于寓言性的东西,并非写实的产物。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在于借神农等远古时代的圣王立说,以便传播道家的人格理想与价值取向。下面试就《庄子》与《淮南子》所描绘的神农形象作简要阐述。
(一)《庄子》所描绘的神农形象
《庄子》,是庄周学派著作的汇编,全书分内、外、杂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书内既有庄周本人的著作,也杂有其后学的著作。尽管该书非一人所作,但思想风格大体相近,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全书集中表达了庄周学派的思想观点,是继《老子》之后一部极其重要的道家经籍。该书提及“神农”共有8次之多其中除《知北游篇》两次(按:该篇谈及“婀荷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时,先后两次提到“神农”,此“神农”据成玄英《疏》言:实“非三皇之神农”)外,其余均指三皇之一的“神农”其人。细读《庄子》,可知其笔下的“神农”,乃是道家从自己的学说需要所塑造出来的人格范型。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将神农说成是“至德之世”的圣王。《胠箧篇》云:“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而(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这段文字中的“神农”,和容成氏、祝融氏、伏牺氏、轩辕氏等一批远古时代的圣人一样,都是“至德之世”的圣王。他们“不以智治国”,而让“民结绳而用”,使民众均受其福,得以“甘而(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不难看出,这一描述旨在宣传《老子》所言:“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愚治主张。我们知道,老、庄从“无为”的基本思想出发,倡导“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庄子》明确强调:“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这些论述,对《老子》所倡导的“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的“愚治”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阐发,它与上述许多圣王治国成效相互呼应,从而使老子“大智若愚”的思想得到张扬。
其二,将神农、黄帝之世说成是“德又下衰”的又一典型。《缮性》说:“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智,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牺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这一段议论,先把远古时代说成是“至一”(即完美而齐一)的美好时代,它“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但是,这个时代到后来日益退化,不断衰颃。一是燧人、伏牺式的衰退,表现为“顺而不一”(即顺从而不齐一,即产生了矛盾);二是神农、黄帝式的衰退,表现为“安而不顺”(即安天下之中有不顺从者,即出现了某种反抗):三是唐尧、虞舜式的衰退,表现为“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即兴起治理教化,使原本淳朴之质遭到破坏,出现了“离道”、“险德”的局面)。不难看出,这里所指的六位古帝所处的时代,分别代表了三种退化模式,其中神农、黄帝所处时代,属于第二类退化的典型。这种把社会说成不断退化的见解,集中表达了道家的退化观念,它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如前所述,神农教民稼穑、遍尝百草而探索疗病之方,以及倡导古代市易,都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庄子》将之视为退化的一代,是有违客观实际的,我们不可信以为真。
其三,把“神农、黄帝之法则”说成“乘道德而浮游”的典型。《山木篇》言:“若夫乘道德而浮游”,“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乎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这里所谓“神农黄帝之法则”,实即庄周学派的法则,其意在以神农、黄帝为依托,说明“乘道德而浮游”主张的权威性。而所谓“乘道德而浮游”,指的是《庄子》所追求的精神自游。这种精神自由,超脱对现实的依赖,而表现为“无誉无訾”(意为不追求荣誉,也不遭受侮辱,实即超脱荣辱)、“一龙一蛇”(意为一时为龙,一时为蛇,能贵能贱,实即超脱社会地位)、“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意为时变我亦变,没有固定形态,实即超脱时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意为能进能退,经常保持心理平衡,实即超脱人事升降),最后达到“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意为与万物之祖即“道”平起平坐,既能主宰万物,而又不被万物所主宰)的境界。显然,这种对现实的种种超脱,意在表达《庄子》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它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实现,因而不可能是“神农黄帝之法则”,而只能是庄子的一种人生理想。
其四,把“神农之世”,说成是“至德之隆”的典范。《盗跖篇》曰:“神农之世,卧在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这里把“神农之世”的社会道德描述为最理想的状况,称之为“至德之隆”,即当时道德达到尽善尽美且无比隆盛的境界,其具体表现是:人民生活自由自在(“卧在居居,起则于于”),一切都很原始朴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人们安于自食其力,且心地善良(“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这一切正是道家所向往的朴真之德。与此相一致,《庄子·让王》也有一段与“神农之世”道德相关的记载:“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通‘禧’),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这里再一次对神农时代纯厚朴真之德作了描述。《庄子》的作者们之所以反复歌颂神农之世的道德状况,其旨在表达“反朴归真”的道德追求。我们知道,在道德取向方面,道家倡导“反朴归真”,《老子》曾明确提出“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庄子·山木》设计了一个“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这个“建德之国”的道德状况,与“神农之世”的“至德之隆”一脉相通,其旨都在于表达“反朴归真”的道德理想。
综上所述,《庄子》所涉及的“神农”,多是构想出来的,意在借圣贤立言,宣扬道家的学术观点。因此,我们不可完全以庄子之描述为据,来评价神农其人、其事。
(二)《淮南子》所描绘的神农形象
《淮南子》是汉初黄老之治的理论总结,集中反映了黄老新道家的学术观点。这部书乃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为探讨黄老之治而撰成的道家新著。它体系宠大,思想新颖,继承发展了稷下道家的学术成果。全书涉及“神农”其人其事共达13次之多。同《庄子》相比,它对“神农”的描述,也具有借圣贤立言的旨意。关于这一点,《淮》著作者已坦诚提及:“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修务训》)这是公开承认其引述神农黄帝之事,具有“托”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它借神农黄帝立言,在许多方面具有黄老新道家的特色。从这一点说,它与《庄子》又有所区别。
其一、歌颂“神农之治”。《主术训》言:“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其民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这里对“神农之治”予以热情赞颂。在作者看来,神农治天下的方法,集中表现为“神化”,即 “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而天下治。其具体表现是,民众朴实、厚重、行为端正,他们不用忿争,而财用充足;不用劳形,而功业自成;因自然所给予的条件,而达到了和同的境界。因此,当时的头领有威严而不用刑杀,刑具搁置起来而不必运用,法律简明而不烦琐,这就是秦汉新道家所向往的“神化”。故又曰:“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戳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这种“神化”的方法,乃是对道家“无为而冶”思想的新发展,特别是强调“怀其仁诚之心”、“ 不施而仁,不言而信”等,都表达了新道家对儒家成果的因袭与继承。显然,这里的“神农之治”,并非真的出自神农,而是当时黄老新道家所向往的治道的思想反映。
其二、把神农等五圣说成是“莫得无为”的典范。我们知道,老、庄等早期道家,强调无为自化,其所谓“无为之治”,带有消极顺应自然的特性,实际上否定了“有为”的合理性。汉代新道家同早期道家有所区别,它对老庄的“无为”作了改造,突出了“有为”的合理性。《修务训》指出:“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象。’吾以为不然。”这里“吾以为不然”一语,表明作者不赞同“寂然无声”式的消极无为。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作者以“五圣”为例,指出:“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这是说,“五圣”都重有为,“莫得无为”(即不搞“无为”)。这里所说的“五圣”,指的是“神农、尧、舜、禹、汤”五位帝王。这五位帝王,一个个都重有为:“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州,南道交趾……”;“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禹沐浴霪雨,……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这些实际例子,都证明“五圣”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有为而治,故作者总结说:“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这就把“五圣”说成是“莫得无为”的典范。强调五圣不搞“无为”而重“有为”,这实际上是用五圣之有为,来改造早期道家的消极无为,从而表现了黄老新道家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其三、把神农等古代“圣人”描绘为“贵因”的典范。《淮南子》十分重视“因”。所谓“因”,就是要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要因势利导,因物为用,因时而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贵因”主张,有意把神农等古代圣人描绘成“贵因”的典范,《原道训》曰:“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泰族训》亦曰:“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苗,粪土树谷,使五谷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这里所说的“因”,不是消极地顺应自然,而是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前提下,积极有所作为。它从又一层面反映了汉代黄老学者积极进取的务实品格。
其四、赞颂“神农之法”。《齐俗训》曰:“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揜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这里所说的“神农之法”,实即黄老道家治国之道。一是强调男耕女织。作者认为,若“丈夫丁壮而不耕”,则“天下有受其饥者”;若“妇人当年而不织”,则“天下有受其寒者”。不仅如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需要靠耕织维持正常生活。故曰:“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揜形”。所以,其强调男耕女织,为的是使天下人不受饥寒;二是主张“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旨在引导老百姓“复归于朴”;三是认为“衣食饶溢,奸邪不生”。这是把衣食等生活必须品作为道德文明的物质基础来看待;四是向往“天下均平”,这是对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均平思想的继承与发挥。总之,这四个方面所包含的“神农之法”,实即黄老新道家所追求的治国之道。
以上我们扼要论述了《庄子》和《淮南子》作者们笔下的神农。揣摩两书关于神农的描述,可知他们所写的神农其人其事,多是作者们虚构出来的,属于寓言性质的东西,旨在借圣贤立说。《庄子》所写的神农,表达了庄周学派的理想追求;《淮南子》所写的神农,则表达了秦汉新道家的理想追求。因此,道家虽然对神农多有描述,但他们所写的神农,多非真人真事。当然,其中有些描述,还是从特定角度透露了某些有关“神农”的传说性资料,如《淮南子·修务训》记述“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 又《淮南子·齐俗训》记载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等,都同历史传说相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史料价值,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