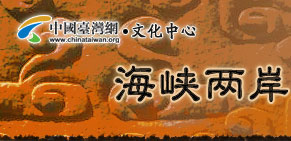楚国雕刻艺术中的炎帝精神
邵学海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研究这个问题,有三个前提要弄清楚。
首先,炎帝属于南方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即传说中的三苗集团,考古学上的石家河文化。学术上这样一个重大学术问题,历来都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炎帝的系属关系。不过,说炎帝属于南方文化系统,不致引起大的争论,这个观点已被大家慢慢接受了。还须说明的是:将炎帝与三苗集团,以及石家河文化相互套合,只能大体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能要求外延的周密,这是因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把这三个概念严密地套合起来。
其次,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上下承传的,任何后来者都不可能摆脱前代的影响。所以研究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自晚明以来一直处于转型的阶段,这期间,发扬传统文化与借鉴它山之石,一直是志士仁人常用的两种方式。在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既然提倡发掘楚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部分,就有必要分析楚文化要素的来源及形成过程。
再三,美术是民族文化的锁钥,它直观、生动、真实、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此我们从楚国艺术的角度,析出楚文化中的原始因素,即炎帝的文化精神,由此认识江汉地区原始文化对后代的影响,并进一步认识楚国历史文化的特点。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变革,在变革中,商周以来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发生动摇,以至于被轻视。代之而起的是重人事、重现实生活的汹涌潮流,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艺术领域呈现一派勃勃生机,因“尊神敬鬼”而滋生的崇高、威严、神秘的审美趣味与要求逐渐淡化了。这时的艺术中,人的地位得到了尊重和肯定,人的需要主导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
这是个遍布黄河、长江流域的大趋势,东周列国概莫能外。但是在楚国,这趋势的演变就要复杂一些,即或青铜器的铸造体现了新时代的风尚,在另外的艺术门类,如漆木雕刻,既沐浴了时代的春风,又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了神秘谲怪的原始色彩。
楚国漆木雕刻艺术具有的浓重的地方特色,恰是楚国艺术之于中原艺术而特别显出的地方。为理解楚人这一情愫,需了解江汉地区以及楚人自史前以来的历史文化背景。
距今约4600年,三苗集团生息繁衍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北缘,大洪山南麓的丘陵岗地是他们的中心区域。这支民族以原始农业为主要产业,并兼有渔猎经济成份,他们种植水稻及蔬菜,饲养家畜,有十分发达的纺织业。制陶业由家庭作坊的阶段,发展成社会化的独立的专业作坊,轮制技术十分先进,甚至,产品的制造也有分工。他们有了琢磨玉器的手工业,产品很多也很精致,并认为人死后,口中含玉可以转生,这时关于灵魂的观念更加复杂和丰富了。他们居住在长方型分间式的房屋里,这个民族可能有了一夫一妻的制度。在地势底矮的地方,可能营造栏杆式建筑。他们还修筑了城堡。最为重要的是,这支民族可能有了冶铜的技术,今天考古工作者在他们留下的遗物里发展了铜矿石和可能用来炼铜的遗物。江汉地区原始社会晚期大致是这样的情形,考古学上称这些史前的遗物为石家河文化。
根据传说,中国原始社会大致分为三个集团,除了三苗集团,黄河中游的为华夏集团;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的为东夷集团。大致在夏初,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已经合为部落联盟,并对江汉平原形成一股压迫之势。
颛顼属于华夏集团,从今陕西、甘肃一带的黄土高原陆续东迁,至了今山东、河北、河南连界的大平原上,首先与东夷集团接触,始而相争,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错混杂,融为一体。宗教改革是两个集团融合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由于地理的遥远,颛顼集团所实行的改革,对江汉平原的三苗集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历史上禹征三苗后,华夏集团把他们比较进步的宗教观念在南方强制推行,所谓“更易其俗”。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根据考古材料,石家河文化区域,仅仅是鄂西北、豫西南一带发生了文化的变异,它说明华夏集团并未到达长江沿岸,他们的宗教改革也未必深入三苗腹地,已经实行改革措施的地方未必能够持久。一直到春秋战国,尽管“重人轻神”的东风吹遍了东周列国,南方仍是人神杂糅、巫风炽盛的世界。可见,原始时期这一社会特征所形成的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新石器晚期始,或者说自原始宗教改革始,南北文化的差别开始显著起来。
充满巫的情怀的楚人,进入到具有深厚的巫觋传统的江汉地区,他们的文化将会出现怎样的面貌?他们的文学艺术又将具有何等的品质?在春秋变革潮流的影响下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异呢?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目前起码有三点可以归纳,在想象力方面,王国维说:“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在情感方面,闻一多说:表现了一种“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崖岩的艳羡。”在形式方面,还是闻一多说:“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自从楚国艺术品陆续出土,楚文化中这种千奇百怪的现象、热烈真诚的情感、变幻莫测的形式,不再是抽象的,而生动、具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所具有的丰富的原始因素倾倒了我们,使我们深刻地理解毕加索何以倾慕非洲的艺术,高更何以抛弃现代文明,融入塔希提尼岛土著部落的行为,他们向往原始,都是为了追求那种没有被所谓道德仁义之类所斫伤的孩童般的情怀。
原始色彩在楚国艺术的各个门类里都有体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其中以漆木雕刻尤为突出。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辟邪,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例子。
马山在楚故都郢都的西北,今属湖北荆州。所发掘的1号墓墓主属士阶层中一位人物,所出辟邪在东周时期所有的楚墓中仅见一件,估计是他生前的玩物。假如提不出反证,辟邪就是一件未经世俗功用影响的纯粹的雕刻艺术,它表现了楚人审美意识的初原形态。
辟邪(其名是暂拟的,究为何物,迄今没有定见)总长69.5、腰高31.5、尾高32厘米,出土时还缠裹着锦衾的残迹,可见这是一件倍加爱护的物品。它用一根委蛇纠曲的树根雕成,主根的一端雕成虎头,头上昂,嘴微张而露齿。另一端雕成蛇尾,蛇尾卷曲。四根分去作为足部,本具有兽类游走、扑腾之状,却被雕刻家雕成了竹节,动物与植物合一体,这大概是仅见的。四根竹节上又分别镂刻了蜿蜒的蛇、鸣叫的蝉、噬雀的晰蜴等等,这就更奇妙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事物,却被和谐有机地揉和在一起。这种奇特怪异的组合造成的感觉难以言表。
辟邪以树根作为媒材,将数个动物的“故事”与神物的“巡游”加以组合,体现了原始初民才具有的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另一件木雕座屏也充满了类似的想象,它是楚人对原始时期,人兽共处之情境的追忆和缅怀。虽然屏面的动物反复表现了激烈的撕杀,但丝毫没有震憾人心的血腥气,倒像一个打逗嬉闹的乐园。
假若说辟邪只出有一件,孤证不立。那么木雕座屏出土了数件。与上述一件近似的,则为2000年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所出。假如数件仍然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楚国的典型器物虎座飞鸟、镇墓兽,分别出有百拾来件,而且都出在楚国的贵族墓葬中。美术样式上,虎座飞鸟、镇墓兽,与辟邪、木雕座屏是有一致性的。
说到形式,必然涉及雕塑的概念。我们知道,它是由长、宽、高三维构成的体量,即空间所环绕的体量之组合。楚国也有这样的作品,如木俑、青铜铸像等,但是楚人特别钟情的,不是体量的组合,而是线性结构与空间的互补与共存,它有些像现代的立体主义雕塑。
立体主义把雕塑看成空间的构成,而不是组合体量的旧传统,从而使雕塑乃空间所环绕的实体这一历史性的要领颠倒了过来,由此雕塑形式变成了一系列被外轮廓所限定的透空或空间的形状。观念的变化,极大地延展了美学的视野和艺术表现的范围。
需要澄清一下,此处并不是标榜我们的祖先,二千年前就有现代艺术的先锋意识,这是很可笑的。这里不过借助现代立体主义的理论,在形式上帮助理解楚国漆器雕刻艺术的意识行为。换言之,楚人这种下意识的创造行为在艺术样式上,与现代人追求的立体主义有相似之处。前面说到的辟邪,鲜明地昭示了这种形式的意蕴,广泛出土在楚国腹地的虎座飞鸟、镇墓兽,则证明楚人的这种喜好已经深入骨髓。它们恰恰带有原始文化的余绪,所表现的集体意识,是与楚人先祖观象授时的神圣职责,以及江汉地区巫的传统相联系的。
关于虎座飞鸟的意义,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鹿角是龙的象征,表明它是龙凤共身的神物,足下踩虎表明除恶辟邪的含义。也有人认为它是古代神话中飞廉的形象,其意义在于招致风伯,让它接引死者的灵魂上天。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要从它的出土地,即先秦时期江、汉、沮、漳的民族关系中找答案。西周以来,这里的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其中文化影响显著的有巴楚两族。巴人和楚人都是北来的侨民,他们因异族的打击先后迁到了巴山、荆山一带,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巴人由西北向东南辗转流徙,楚人由东北向西南不断拓展,他们在今湖北的西部相遇并紧紧相邻。与山地比较起来,江、汉、沮、漳是他们必欲取之后膏腴之地。无庸置疑,楚人和考古材料,春秋早期,巴文化在江、汉、沮、漳的势头强盛。到了战国,这里的巴人及土著,逐渐被楚人同化,巴文化及土著文化融合进楚文化中去了。
然而,凡文化交流都是双向或多向的,楚人夏化蛮夷的同时,也会吸呐蛮夷文化的因素,具体到江、汉、沮、漳,主要是吸纳巴文化的因素,表现在艺术上,则是楚国艺术中出现虎的现象。虎的现象在楚国郢都一带出土的艺术品上表现得最为显著。
巴人崇虎,虎是巴人祖先的图腾。楚人崇凤鸟,其渊源可追溯到高辛部落。楚人的虎座飞鸟之虎座,当是体现巴人原始宗教的意义,他们将自己的灵物安装在了巴人的图腾之上。
分合、转化是原始艺术常用的两种手法,十分典型的例子如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它是将某一物的自然属性附会到主体物的身上,以强化主体物的神性。或者将数种物性加以组合,以体现新的神性。玉器神徽属于这一类。这是一种类似儿童想象的原始思维,文化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种思维不是在记忆中复演旧经验,而是将已有的意象混沌地综合起来,它不象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而是不回避矛盾。所以这种思维又称原逻辑思维,它反映在艺术形式上是因果关系不明了,也不易理解与分析。但其竟象往往出人意料,令人惊愕与赞叹。
代表楚人宗教观念的象征物为什么要加上巴人的老虎?上古时期各民族崇拜的灵物都是绝地通天的工具,巫觋借助这个工具去取得上帝的意旨然后降于人间。同样,人是灵魂也可以搭载灵物归去,战国中晚期的制画也描画了这个意思。夏商之际,或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各个民族的宗教神灵并不相同,而且这些神灵分了等次,等级的高低是根据它们的速度而定。灵物的速度在祭祀时十分重要,晋代《抱扑子》说:道教上天入地“周流天下,不拘山河”之法有三等,一是借助龙,二是借助虎,三是借肋鹿。张光直认为,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龙、虎、鹿的蚌壳摆塑,就是道教龙蹻,虎蹻,鹿蹻的端绪。后来随着社会组织的合并与重组,图腾意识减弱、消失,灵物意识逐渐增强,不同民族的神灵变得可以通用或同构了。那些声名显赫的灵物,如龙、凤、虎、鹿等等,也成了天下的公器。
巫觋借助的神灵主要有龙、虎、鹿、凤等,随着西周以来“以德配天”思潮的兴起,各个民族开始改造各自的灵物。至了春秋,这些灵物的形象基本完善,如越人崇奉的龙的头上,长出了楚人崇奉鹿角,替换了商人欣赏的柱形角。如北方民族崇奉的兽类,插上了东方民族崇奉的凤鸟的翅膀等等。本来,楚巫借助的神灵是飞廉,飞廉是楚人的巫蹻的速度,在改造灵物的风气下,楚人就近将巴人的巫蹻与自己的巫蹻组合,在他们看来,多个巫蹻的效果一定比单个巫蹻好得多。
虎座飞鸟原逻辑思维的色彩要淡薄一些,它的构成要素,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其意义的路径。镇墓兽原逻辑思维的色彩则浓重得多——这个神秘谲诡的雕刻作品,拉起了厚厚的面纱,它拒绝提供哪怕粗略的线索,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神秘的无可言传的意味。所以对它的定名五花八门,有说是“山神”、“辟邪”、“土伯”、“战神”或“兵主”,也有说是引魂升天的龙、灵魂的看守者,冥府守护者和灵魂的化身等等。这些说法相互抵牾,由此体现了原逻辑思维不排斥矛盾的特性。
虎座飞鸟与镇墓兽的“功能”,体现了楚人对生与死的看法,它的形成蕴藉了楚人一直保留着的对苍天的敬畏和向往之情感。甚至,它的要义或是对先祖司天之职的缅怀念与追念。楚人冥器的这种线性伸展的样式,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楚人在埋葬死者时所追求的,已经艺术化了的宗教境界——这境界分明也是艺术化的深邃的空间。
第一,楚国漆木雕刻艺术,把人类童年时期所具有的一种天真、忠实、热列的情绪,极好地延伸下来,它强烈鲜明、缤纷五色,显示了楚人身上没有褪尽的原始情结以及审美心胸。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们的作品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和犹如面对儿单般温馨的情感。
第二,楚国漆木雕刻艺术,体现了无羁而浪漫的想象,这种源于原逻辑思维方式的心像,正是对于空间的理解和追求,首先,它一系列外轮廓分解了空间,使空间成为雕刻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次,由天然的叉丫张扬的材料所构成的四向伸展、辐射的形式,使观者产生了轻盈的,似乎可以融入空间的升腾感,这种艺术的感觉是神秘、畅快而令人鼓舞的。
上述两点,是保留在楚国漆木雕刻艺术中的炎帝时期的优良传统。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