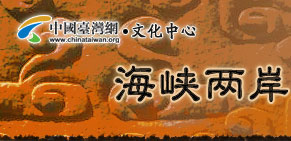作者:梅 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明代的香税以泰山和武当山的数量和影响为最。武当山香税的征收始于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是明代最早征收香税之地,由湖广布政司和提督太监委派的官员即均州千户所千户和太和宫提点负责。打着维修庙宇的旗号而征收的香税,在嘉靖以后还用于赈济灾荒,抵宗藩、官军俸粮之不足等事项,正是明代中后期国家政治腐败、财政危机、加派风行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香税;明代;武当山
香税,是明清时期国家对朝山进香信士征收的一个特殊税种。进香需要纳税,还设有税官进行管理,这在明以前尚未见到。明中叶以后,民间百姓借烧香进行旅游的人流蔚为壮观,这为政府香税的征收提供了可能。关于香税的定义,明查继隆《岱史》卷十三《香税志》曰:“曷云乎香税也?四方祈禳之士女捧瓣香谒款神明,因捐施焉,而有司籍其税以助国也。夫概天下香税,惟岱与楚之太和山也。”这说明香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补充部分,具有确定的税率及强制性等特点。但此言明代仅泰山和太和山即武当山有香税的征收则不妥,一般论著也认为明迄清初只有泰山与武当山曾征收过香税 ,事实上,明代及清初还有多处香火旺盛的宗教圣地都有征收香税之举,如涿州(即今河北涿县)的丫髻山 ,延安肤施县(治今陕西延安)太和山 ,南直隶的云台山 、号称“江南小武当”的齐云山 等。我们推测明中叶以后,相当一部分香火颇旺的宗教圣地,可能都曾征收过香税。从香税的数量和影响上来说,则以泰山和武当山为最。
目前所知国内学者最早对泰山香税进行研究的当属韩光辉。他的《泰山香税考》一文对泰山香税的源起、税额、征收和使用及香税的裁革进行了考释 。此后有关泰山的著述也多载有泰山香税征收的情况,大体上沿袭了韩文的观点 。成淑君则从泰山香客的角度,系统分析了泰山香税对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 ,弥补了韩文所缺。日本学者□(三点水加尺)田瑞穗对泰山曾作过专门研究,有《泰山香税考》一文,可惜笔者没能拜读到。有个别财政史著作对香税问题也有涉及,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六章杂色收入讨论到香税:税源来源于武当山与泰山,每年的收益达到4万两白银;两地名义上由礼部管理,由其负责两地寺观的维护和修缮,但实际上香税是由两地的太监征收 。
关于泰山香税问题,明代查志隆的《岱史》卷十三《香税志》有明确的记载,明清文人和相关志书亦多有记载,故征收情况较明确,目前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而对武当山的香税,因明清山志语焉不详,尚无专文予以研究,目前仅见有杨立刚在讨论明清时期武当宫观经济收入时对武当香税的缘起、征用及废除略作有考证 。作为明代与泰山齐名、香税收入不相上下的宗教圣地,武当山的香税收入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武当山的宫观经济,也关系到社会文化史诸问题。下面以明清武当山志、文人记述和笔记及存留于武当山的碑刻为材料,对武当山香税的征收、数额、管理、使用等情况进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 武当山香税的征收与管理
武当山香税的征收始于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七《敕存留香钱》记载弘治六年,均州民蔡杰奏奉钦依礼部议定:“每年正月起至四月终止,委官于太和宫金殿内,收受香钱,解送均州净乐宫官库收贮,以备修山各项支用。” “其五月以后香客稀疏,所舍香钱定从提督官员收受,以备岁时焚修之用” 。其征收时间早于泰山。泰山香税始征于武宗正德十一年(1521),比之武当山晚了23年。而上文所引南直隶云台山、延安肤施县(治今陕西延安)太和山则至嘉靖年间(1522-1566)才有征收,如杨茂《太和山碑记》云:“县治之西南里许有山焉,层峦叠嶂,洛水绕于其下,嘉靖初年感白兔呈祥之异,创建玉台观于上,彼时明神感应捷若,影响四方来朝者,自二月至三月朔旬香客络绎不绝,香资每至一二千金,洵上郡第一奇观也。然庙地系留西里匠刘襄阳地,彼时匠价及住持焚香度费香税及之。厥后,香税入官,而各费用咸无所出。……有名山方有香税,有香税方有名山。兹本山香税既已入官,可令常住之地复有粮乎?可令烧香之人复被挠乎?”此碑记述了太和山嘉靖初年建玉台观后始有香税的征收,用作庙地和主持焚香的费用,后香税被官府所收,只留极小一部分给观中常住之人。云台山香税的征收比照于泰山例,足见其征收晚于泰山。齐云山香税征收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之后。从已见文献来看,明代香税最早开征于武当山。
武当山成为明代香税最早的征收地与明代真武信仰的兴盛、永乐年间武当山宫观的大规模营建、武当山地位的上升、武当道教势力的发展和武当山对香客的吸引是分不开的。自永乐间大修宫观后,全国各地朝武当的信士信女日益增多,自愿布施捐献的钱物如云委川赴,源源不断。这些钱物虽有用于宫观维修等正当开支的,但也有相当部分被几任提督太监私吞。如在成化十五年(1479),湖广右参议韩文提调武当山,就曾没收太监陈喜贪污宫观的香钱,买粮万石备赈。正因为管理无度,贪污严重,这才有弘治六年蔡杰的上奏,请求征收香税于太和宫。
武当山香税的征收和管理由藩臣和内官共同负责。明永乐年间(1403-1424)为控制武当道场,成祖亲自委派藩臣即一名湖广布政司右参议常驻武当山,为全山的总提调官,组成管理机构,负责全山所有事务。藩臣公署设于均州城,下辖均州千户所等机构。宣德十年(1435)以后,增设内臣提督府,与藩臣提督府共同管理全山事务。香税由提督太监与提调参议委官员负责,具体征收由湖广布政司和提督太监委派的官员即均州千户所千户和太和宫提点负责。
最初征收时,千户和提点分别在不同的时段征收: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七《敕存留香钱》记弘治六年(礼部)“令湖广布政司每年正月至四月香客盛行之时,委官收受香钱解送均州净乐宫官库收贮,以备本山修葺庙宇之资,其五月以后,香客稀疏,所舍香钱听从提督官员收受,以备岁时修焚之用。”即千户在一至四月征收,太和宫提点在五月以后收。从嘉靖十年开始政策有了改变。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七记礼部令云:
自嘉靖十年为始,一年香钱通行委官收受,填注簿籍。查照先年题准事例,四月以前所得香钱仍贮均州净乐宫官库,以备官军折俸及提督官员门隶雇直;五月以后,所得香钱收贮本山官库,以备本山岁用香烛油蜡,道众冬夏布匹及修葺殿宇;如遇半年果有羡余,岁岁储积以备凶荒。仍将每年支用过数目置立文卷,申送巡按御史处以凭照制。世宗下圣旨说:“是,这香钱只着照旧例行。”
“一年香钱通行委官收受,填注簿籍” ,藩臣和内官征收香税不再区分时段,而由他们所委派的均州千户所千户和太和宫提点共同在太和宫负责征收。所以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崇祯年间考察武当山时,在金殿见到“督以一千户,一提点,需索香金,不啻御夺” 的情形。
武当山征收香税的政策一直沿袭到清中叶。王澐于康熙十二年(1673)游武当山,其《楚游纪略》载,金殿“殿旁二小室,左以憩客,右有司香税者,曰:‘税不及千金,以给军兴费矣’”。香税数量与明代不能相比。乾隆元年(1736)太和山香税始废除。《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50云:“湖北太和山香税,照山东泰安州之例,永行豁免。”泰山废除香税的时间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次年四月十三日乾隆下诏:“山东泰安州香说,朕已降旨豁免。近闻湖北太和山凡远近进香者,亦有香税一项。小民虔礼神明,止应听其自便,不宜征收香税,以滋扰累。所有太和山香税,著照泰安州之例,永行豁免,该督抚即饬令地方官,实力奉行。毋使奸胥土棍,巧取滋弊。” 直到今天,武当山仍保存有“豁免香税碑”,碑立金顶朝拜殿内,高1.4米,宽0.7米,厚0.1米。正书16行,行35字。
有关武当山香税的具体数字,史籍无明确记载。《通雅》卷21云:“武当、岱岳,今最感重。永乐建真武庙于太和山,几竭府库,设大珰及藩司守之,而二庙岁入香银亦以万计。”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74均说 “岁入香银亦以万计”,《五杂俎》则称“常数万缗”(见下引)。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列泰山和武当山香税额为四万两,这还只是上交给国家的税收。虽然具体数不明,但从香税的用途中可窥见香税数量的巨大。
二、 香税的使用
武当山香税的收入,主要用途一是支付宫观的维修费用和宫观日常用度。明初,武当山建筑的修理费用和各宫观香烛油、蜡、布匹等均由国库开支 。日常修理宫观,购买必须的材料,先是“俱派襄阳府所属州县动支钱粮,差官买办料物解用”,弘治六年(1493)以后则奉旨由香钱中支给 。嘉靖二年(1523),提督太监潘真、郧阳抚治徐蕃各题本上奏,建议将香烛油蜡及布匹俱在本山香钱内支用,不必动用官银
嘉靖十年钦差提督太监王敏题“永乐十五年修建本山宫观,落成之后,荷蒙太宗文皇帝派定祀神香炷油蜡每三年共计三万七千二百八十四斤,香油二万二千五百一十二斤,黄蜡九百二十四斤,降真香一万一百二十三斤,宿香三千七百二十五斤蒙钦赏;官道每年冬夏布匹四千八百匹,勘合类行湖广布政司坐派襄阳府所属州县于夏税内折征解纳供给,百五十余年不缺。嘉靖二年前任提督本山太监潘真适值丰稔之年,各处香客颇众,彼时奏奉钦依免派于民,改令本山香钱内支用(均州千户所官军折色俸粮也在香钱内支用),委惬众议。” 。
世宗同意了这一节省国家正税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实行百年之久的陈规。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明末。志书中多见有动用香钱维修宫观的事例。嘉靖二十一年(1542)正月丁亥,督木都御史潘鉴奏:“湖广该楠、杉板木一万余根,应费银五十七万两,今仅得七万两,乞将本省……太和山香钱……留济急用。” 隆庆三年(1569)五月壬子,“提督太和山太监柳朝乞留岁收香钱银四千三百余两,修理本山。上从之” 。
二是支付官吏的俸禄。谢肇淛《五杂俎》称:
武当元君二祠,国家岁籍其香钱,常数万缗。官入之,以给诸司俸禄。不独从民之便,而亦藉神之贶矣。然官吏饩廪,自当有惟正之供,取足于此,似为不经。所当入之本州,以为往来厨传之费,免加派之丁粮则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终,藩省辄遣一正官至殿中亲自检阅,籍登其数,从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盗然,谓之“扫殿”。而袍帐、化生、俚亵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武当亦然。
谢氏虽极力主张官俸应自有来源,不应用此香钱,建议所入香税应当收入州府,用作往来的费用,以免加派百姓,但也从一侧面说明地方奉禄不足,需从香税中支取。先前,武当山“提督太监员下日用禀给口粮并额设门皂俱在所属州县均徭内遍佥解纳”,嘉靖元年(1522)该抚治郧阳都御史徐蕃“议得地方灾伤,今复免派于民,只于太和山之香钱供太和山之守臣”;嘉靖二年均州千户所折色俸粮亦由香税取给,仅这一项开支就有“数千两”白银。
三是嘉靖元年(1522)以后,由于国库逐渐空虚,各方官僚常常题奏索取武当山香税用于赈济灾荒,抵宗藩、官军俸粮之不足,见于《明实录》,有如下记载:
嘉靖元年(1522)五月丁卯:湖广抚按等官以常赋拖欠、蠲免数多,宗藩禄米、官军俸粮不足,请动支……太和山香钱二年……许之。(《世宗实录》卷14)
嘉靖二年闰四月癸丑:诏蠲太岳太和山香钱一年备赈,从湖广守臣奏请也。太监潘真奏留,不许。(《世宗实录》卷26)
嘉靖三年二月辛酉:以湖广民饥,发太和山香钱二千两赈之,从巡按御史马纪清请也。(《世宗实录》卷36)
嘉靖五年八月丙寅:以灾伤诏……发太和山香钱赈济饥民并补月粮之缺。(《世宗实录》卷67)
嘉靖五年十月戊寅:以湖广灾伤……仍发太和山香钱赈济。(《世宗实录》卷69)
嘉靖十四年三月己卯:先是,以湖广旱灾从抚臣议发太和山香钱充赈,至是,提督太监李学请存留供祀。户部议:“将嘉靖十三年以前者尽数发赈,并补给禄粮月俸;以后者仍遵照题准事例委官收领,四月以前者贮均州库公用,五月以后者贮本山库备用。”(《世宗实录》卷173)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户部奏:“湖广武昌府属灾伤,请将……太和山香钱……赈济。”报可。(《世宗实录》卷218)
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壬子:时湖广旱甚,户部请留……太和山香银……备赈……诏从之。(《世宗实录》卷290)
嘉靖三十年十一月丁亥:以太和山今岁香钱及明年之半抵补显陵官军奉粮及赈济所属灾伤人户。(《世宗实录》卷379)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癸丑:都给事中刘弘宝劾武当提督太监黄勋,谓:“工部原议本山解银一万两,织造本宫顶帐,勋止解四千有奇,大是欺抗。请照旧例会同司道收支香税,发仓备赈。”奉旨:“本山量解七千两,工部补足三千两。”(《神宗实录》卷270)
此外,《续文献通考》卷32亦载“嘉靖五年(1526),湖广发生灾害,取太和山嘉靖四、五两年香钱十分之六赈湖广灾。”《明史》卷227《郭惟贤传》载万历中“请以太和山香税充王府逋禄,免加派小民”。
其他如制造坛场供器、建醮费、进贡土产置办费及运费等无不从香钱内动支。足见武当山香火的炽盛,香税收入之多。明人甚至因此称武当山“富甲天下”。
明代,武当山真武大帝的神名远播,香火兴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香客前往进香朝拜。为表示心诚,四方香客来祀真武,往往大量施舍金银等物,使得政府从中找到了赚钱的机会。弘治六年香税的设立,使香客布施的金银和应交纳的税金有了统一的管理,结束了前此的混乱局面,增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当地民众的负担。这是广大香客为武当山地方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三、香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武当山香税的征收名义上由藩臣与内官共同负责,但明中叶以后,随着宦官势力的膨胀,武当山提督太监的权利和职掌逐步扩大。成化十二年(1476),为监视镇压荆襄流民起义而驻守于武当山的武官——提督太监还兼分守荆、襄二府所属州县并卫所,不久,管辖区域扩大到荆、襄、郧三府及河南南阳、陕西汉中、西安等府与郧阳交界的各县,凡这些地方发生的军政大事,均由分守太监会同镇守总兵与地方官共同商议,上报朝廷。此后一直到明末,其间仅隆庆年间(1567-1572)“毋兼分守”外,提督太监多兼分守。因此,武当山事务名义上虽由内臣与藩臣共同管理,但事实上,内臣往往凌架于藩臣之上。
具体到香税的征收也是如此。隆庆四年(1570)十月三十日,敕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李存文:“本山香钱,会同内臣选委员役收支” ,但实事上往往由内官主之。《明实录·穆宗实录》卷32“隆庆三年五月壬子”条载户部尚书刘体乾言:“太和山香钱岁入不止此数,旧虽守土藩臣与内官共理,而收掌出入多内官主之。宜比山东泰山事例,令抚按官选委府佐一员专收正费之外余银,尽解部供边,其修理诸务,俱命有司董之,内官不得干预。”疏入忤旨,令自陈状。刘体乾上疏曰:“臣愚不能将顺明命,冒渎天威,罪不容诛,但以职司钱谷,目击时艰,窃不自揆,欲为朝廷节财用耳。”上责体乾不遵明旨,屡次奏扰,夺俸半年。武当山宦官势力的膨胀,使朝中大臣十分不满,他们屡屡上奏,建议武当山的香税管理应如泰山例,由藩臣负责,然均无成效。
在香税的使用上,隶属于湖广布政司的藩臣考虑的是地方的利益,常常上奏请求动用或借用香税赈济省内其他地方的灾荒、抵官军、宗藩俸粮之不足,而提督太监则上奏反对,笔墨官司打过不停,常需皇帝予以定夺。这在明代凌云翼、卢重华的《大岳太和山志》卷三《列圣敕谕·敕存留香钱》中有诸多记载。
官员的贪污与挪用现象也很严重。为此朝廷常委派官员清查香税,如嘉靖八年(1529),太监王敏等奉旨清理武当山香钱。正是由于香税数额的巨大和管理的混乱,征收香税之职被视为肥缺,人人争营之。不仅在明代如是,即使在香税额减少的清初亦如此。光绪八年《麻城县志》卷十九《耆旧志·仕绩》(278):“胡耀龙字群吉,公国子。顺治辛卯举人,壬辰进士。任郧阳府教授,时府经兵火,黉宫未及修理。耀龙捐资重建。值西山遗孽跳梁频年,大兵进剿委给粮行间,士无哗者。连摄郧竹房三县。篆武当香税典史者旧有例,人争营之。耀龙两委监,不受一钱。”从胡耀龙“不受一钱”而被书传者特意提出来看,足证收受银钱则为常有之事。
香税征收本是为维修宫观,后渐扩大至宫观日常用度和官员的俸禄,至嘉靖年间以后还常以借贷的名义挪着他用。为此,嘉靖(1522-1565)、隆庆(1567-1572)年间皇帝曾数次下旨,不许有司借贷。如嘉靖十七年(1538)三月,“礼部为遵敕谕清明旨存留香钱免借贷以便祀神修理预备凶荒赈济事,奉世宗肃皇帝圣旨:‘是。这香钱着存留本山备用。不许有司借贷。礼部知道。钦此’。”但事实上,此事屡禁不止。隆庆二年(1568),皇帝曾下圣旨:“武当山,玄圣之处,是我祖宗佑国保民之际,如何这等紊乱。都着照旧行,礼部知道。钦此。”但第二年,钦差提督大岳太和山内宫监太监柳朝“复题前事” 。实事上,从上述所引香税用途的史料来看,香税用作他途也是皇帝许可的。其实,打着维修庙宇的旗号而征收的香税如此施用并不奇怪。这正是明代中后期国家政治腐败、财政危机、加派风行的必然结果。
香税的征收对象为香客,而香客的多少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武当山绝大部分香客为普通民众,朝山人数与香客的收入特别是来源地年成好坏有关。因此,香客每年的人数不等,香税的收入因之也有较大的区别。而宫观的日常费用则基本上是固定的,因此,香税收入多时,费用尚够,或有盈余,香税收入大幅度减少时,则入不敷出,影响到宫观的日常用度和宫观的维修。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七《敕存留香钱》记嘉靖十年钦差提督太监王敏题“嘉靖二年前任提督本山太监潘真适值丰稔之年,各处香客颇众,彼时奏奉钦依免派于民,改令本山香钱内支用(均州千户所官军折色俸粮也在香钱内支用),委惬众议。奈连年各处荒旱,香客稀少,香钱不敷支用,致将香炷油蜡自嘉靖元年起至嘉靖十年止俱至欠少,道众冬夏布匹已支过六千六百四匹外,欠一千三百九十六匹有余等因各申到,臣访得远近大小人民万口一辞,亦谓香火大异往时”;嘉靖二十一年三月钦差提督王佐奏称“今玉虚宫东桥青羊涧桥并会仙桥至大顶一路石栏板踏垛等项,已经修理二年,尚未得完,盖因连岁临境灾伤,各处香客稀疏,以致香钱短少,所以不足支给应用也”。
此外,香税的征收,影响了朝武当山的普通民众的人数。明清两代武当山每名香客缴纳税金的数量,因不见于史料的记载,今已不可详考。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7《敕存留香钱》记太监王敏言:“臣自任事以来,仅得二载,正值年岁荒歉,每年正月起至四月终止,香钱虽经委官收受,不及各项支用。臣看得本山香钱缘非额定之数,随其时岁丰欠,任其多寡施舍,预难逆料;秋冬两季,名虽余月,香钱实以截长补短,相凑公用,委的岁入不足岁出”。从“臣看得本山香钱缘非额定之数,随其时岁丰欠,任其多寡施舍”的字样,武当山的香税没有定额,而是随香客的意愿。嘉靖三十一年(1552)正月因承天府等地发生水灾,湖广布政司呈请借用武当山香钱一万两赈灾,提督太监王佐上奏表示反对,他说:
太和山香火全赖湖广河南两省军民进香施舍,三十年湖广合省自春以来亢旱不雨,至秋又遭水患在在处处救死不暇;河南地方又因边方有事供给军需奔趋公役,至于十月间方有香客朝山,止是了还愿心而已。虽有所施不多,除节因修理公用等项之外,见在官库收贮银钱不及百两,其出入之际,自有本宫提点公同州所官吏眼同见数备申该道右参议雷贺处俱有卷案可照。其称三十一年香钱未经收受,难以逆料,见今缺欠二十九年分均州千户所官军折色俸粮并玉虚等宫观官道冬夏布匹,三十一年供神香炷油蜡合用钱粮无从挪移出办,岂有蓄积隐匿。
从他所奏“至于十月间方有香客朝山,止是了还愿心而已。虽有所施不多”来看,似乎武当山香税亦无定额。上引徐霞客和王澐文也不见香税的具体数,这与泰山有很大的不同。据韩光辉的考证,泰山香税实行之初,内外有别,本省香客每名输银五分四厘,外省九分四厘。可能是内外之人不好区分,万历八年(1580)内外统一为八分。此后,香税的数量不断上涨,到万历末年增至一钱二分,到崇祯中后期,则达到一钱四分。明代后期税重可见一斑。清代恢复到初始征收的水平,内外有区分。但无论如何,香税决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强行征收。这从上引徐霞客文可知。而且,从武当山与泰山的香税总数不相上下来看,朝武当的香客所纳税金当与泰山差不多。香税的征收对普通百姓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武当山宫观庙宇群庞大,且较为分散,香客逢庙必进,逢神必拜,施舍香钱的数额颇大,加之金殿香税的付出,往返的路费和一路上的开支,相对于香客的收入,朝一次武当山的费用是巨大的,以至于当时流传着“穷不游武当,富不登太白”的谚语 ,这无疑会减少一部分普通民众朝山的人数或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