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生日,今年是她诞辰95周年。而最近又有一部她的遗作在大陆出版,使得我们有机会能以“读”的形式去纪念她。这部作品就是她用英文写作,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爱情故事为主线的小说《少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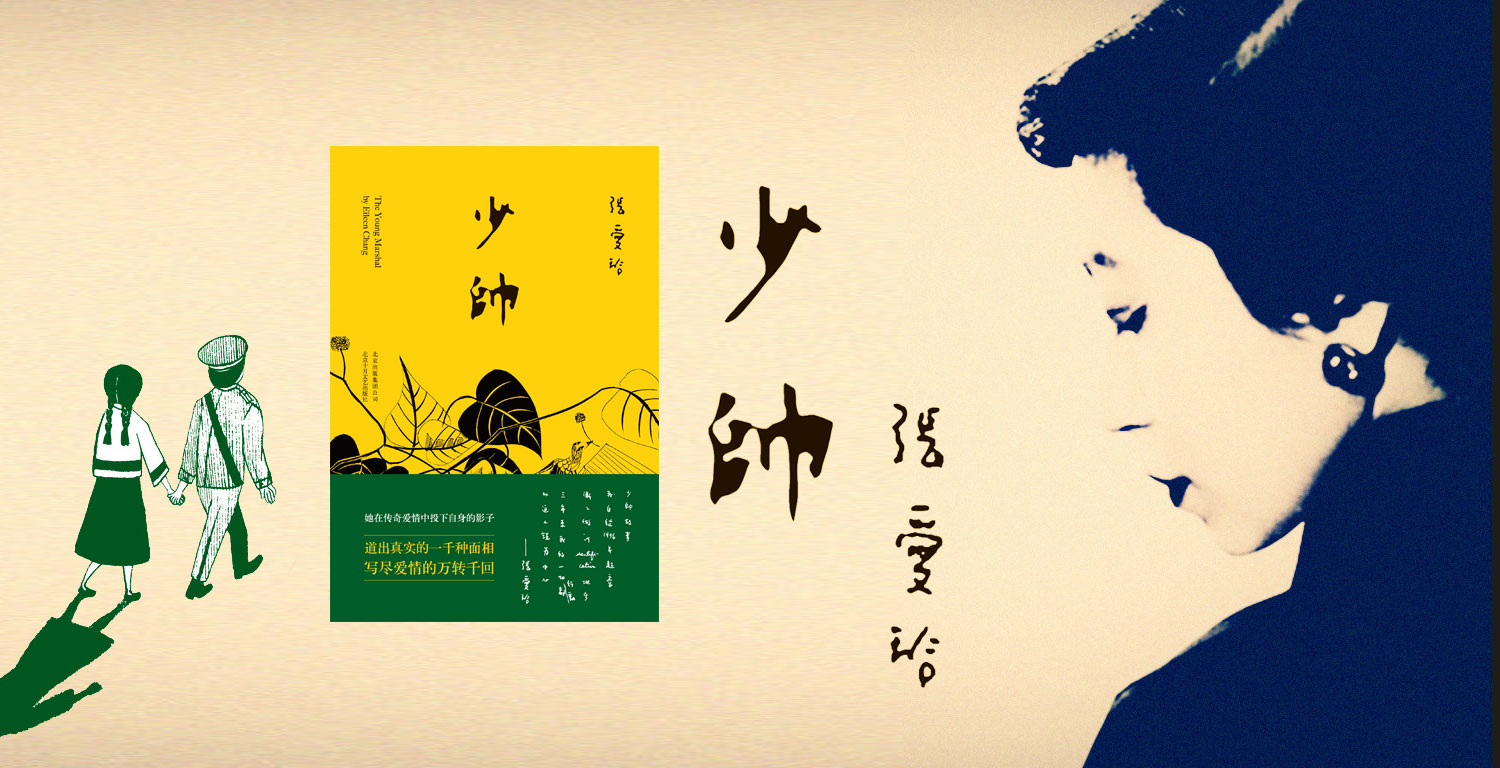
一本仅有七章,英文约2.3万字的小说,从找定译者、着手翻译到最终出版,竟用了三年时间!考虑到翻译张爱玲作品的不易(既要英文水平好又要熟悉张爱玲),宋先生找来了本来就是张迷、自己也在做翻译的郑远涛先生。翻译很快出来,大约用了三四个月,修订却做了很久。用冯睎乾先生的话说就是修改了“无限次”,“他译完,我校,他再译,我又再校,好像永远也做不完。”结果是宋先生只得“给他们一个限期”。而冯先生把自己梳理张爱玲为写小说参阅的书籍、核实相关史实的过程,比喻成“福尔摩斯查案”:“自己也好像在写小说,因为正在诠释别人怎样诠释一些事;当你诠释时,你已加入了个人的文学想像,再去诠释那作品,便成了双重想像。就是在一个想像的世界中,再想像另一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最后好像在写侦探小说,只不过是用历史人物做角色,他们有的真实有的虚构,并以文学批评为背景。”
——《少帅》编辑手记
关于《少帅》
《少帅》是张爱玲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为蓝本,耗费十年以上的时间蒐集资料而撰写的小说,最後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一直是文坛的一大悬念 与遗憾,如今,这部传闻已久的神秘作品,在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努力下,终於得以呈现在所有读者面前。张爱玲利用小说的形式,透过深富「人生味」 的历史轶事来描绘「另一个时代的质地」,也隐隐透射出她自己的影子。《少帅》可以说是张爱玲最後一部未曾刊行的小说遗稿,从今而後,将再也没有其他重大作 品可以出土了,本书之珍贵,也由此可见一斑。
故事始于正值军阀时期的北京,十三岁的周四小姐恋上了潇洒不羁的少帅。在一次帅府宴会中,少帅主动赠予周四小姐一把扇。他们很快地恋爱了,彷佛这是件再自然也不过的事。
大时代的纷扰也无法阻挡彼此的绵绵情意,风流倜傥的少帅和娴静纯真的四小姐,他们之间的爱情既内敛又奔放,既婉约又灼热,就像正在转变的中国,渴望崭新的未来,却也无可避免地守旧。然而,在这深宅後院里,又将会有什麽样的考验等待着他们?……
1964年小说写出约三分之二,1966、1967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她还表示要继续写下去,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现存英文打字稿八十一页,共七章,约2.3万字。
在这部寄托遥深的小说里,张爱玲承继含蓄蕴藉的古典小说传统,以一贯擅长的如工笔画般的细腻笔触,讲述了在“荒废、狂闹、混乱”的大时代里,少帅和周四小姐似真如幻、无望而又亘古如斯的爱情故事。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外面的世界乱糟糟的,但透过四小姐的窗口望过去,他们是仅有的两个人:她沉浸在这样的刹那,以为那就是永恒;她身不由己地加入延续千年的爱情长程,却发现自己淹没在面目模糊的女性队列中……
少帅故事我自从1956年起意,渐渐做到identification地步,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小说为中心。
——张爱玲
小说题材太好了,大时代背景,时代造成的英雄人物,然后有一段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
——宋淇
其实在我看来,要去先读读《倾城之恋》,两部小说是有关联的。在《倾城之恋》这个爱情故事里,范柳原和白流苏其实是没有前途的,但一场战争成全了他们。同样,少帅与四小姐也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之间可以有一段情,但不可能过一生,结果因为一场事变,成全了他们。
——宋以朗
《少帅》就是这样一本深入浅出充满夹缝文章的书。它每处细节都体现着整部小说的主题,仿佛一个碎形(fractal),一花一宇宙,一字一菩提。在张爱玲笔下,历史也许只是一场幻影,唯有人的无明爱欲才是永恒。在这层意义上,《少帅》其实已经写完,却永远不可能读完。
——冯睎乾
《少帅》摘句
现代史没有变成史籍,一团乱麻,是个危险的题材,绝不会在他们的时代笔之于书。真实有一千种面相。
娉娉袅袅十三余,
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
卷上珠帘总不如。
她觉得自己隔着一千年时间的深渊,遥望着彼端另一个十三岁的人。
她一动不动,迎风光裸着。他的手臂虚虚地笼着她,仿佛一层粉膜。她惘然抵抗着。他一定也知道是徒然。由于他们年岁的差别,他很早以前就娶了亲,犹如两人生在不同朝代。她可以自由爱恋他,仿佛他是书里的人。
他爱她。随他们说媒去,发生什么她都无所谓了。他爱她,永远不会改变。居然还是下午,真叫人惊异。舞台上的锣声隐隐传来。她寂寞得很,只能去触摸游廊上的每一根柱子每一道栏杆。又拐了个弯,确信他不会看见之后,她的步子跳跃起来,只为了感受两根辫子熟悉的拍打落在肩膀上,不知为何,却像那鸣锣一样渺茫了。
在一个乱糟糟的世界,他们是仅有的两个人,她要小心不踩到散落一地的棋子与小摆设。她感觉自己突然间长得很高,笨拙狼犺。

《少帅》真幻
——宋以朗、冯睎乾、郭梓祺三人谈
宋以朗:张爱玲遗产继承和执行人
冯睎乾:张爱玲研究者
整理考证:福尔摩斯探案般的三年
郭:你们是何时开始的?
冯:张爱玲写三年,我们便写三年。
宋:那即是二○一一年。有些人很憎我,说我把张爱玲的东西藏起来,几年才放一本出来,像“挤牙膏”一样。但我觉得出版《少帅》颇难,要计划整个过程。她之前的《易经》和《雷峰塔》都是自传体小说,如要找人写序很简单,到台湾找张瑞芬教授就是,因她研究张爱玲,清楚她的个人历史。出版张爱玲《老人与海》译本时,找了住在美国的高全之写序,也容易。
到《少帅》就麻烦了。有些人看过,说小说好像不符事实,那便要先查清楚事实。接下来,不符事实处就要思考因由了。是否张爱玲的工夫不足?抑或她是刻意写成这样?如刻意,又为了什么?我当时想,找人写序要求很高,该找什么人呢?找个张爱玲专家,他对张学良或不熟悉,如我要求他核实历史事实,是要很大工夫的,他也不一定愿意投放时间。如果找个历史专家,他又不熟张爱玲。我觉得没现存的人是两门都可以的,唯有逼冯睎乾,跟他说麻烦你了。
冯:其实我两门学问也不懂的。
郭:但我在《少帅》附录文章,看到你搜集资料的过程,如试图找回张爱玲那几年可能读过的书和杂志,就觉得不能想像,简直是大海捞针。
冯:是不能想像的。
宋:最初不知如何开始,我先到书店,看有什么张学良的书,一见便买。
冯:可是张爱玲有未读过这些书,这是最大问题。
宋:过程中,觉得张爱玲提过的一本书很重要,便去找,那就是 Donald of China。
冯:那时发现在理工图书馆有一本,因为是参考书,不能外借,所以我直接在那里复印了全书,然后马上寄给在北京的翻译郑远涛,跟他一起读。
郭:张爱玲在信中曾说,这书其实写得不好,是吗?
宋:八卦的内容多的是。
冯:这是Donald亲自忆述,当然也有些内容可能是错的,正如张学良的口述史也会出错。
宋:但你问怎样寻找数据前,应先问为何要寻找。
郭:那原因是什么?
冯:一开始,宋生只是说,书出来时不要给人告诽谤。他怕张学良的家人质疑,张学良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因为小说写周四小姐当时只有十三四岁。你又怎知道这些是真的?故需比对史实和小说,原本打算写一篇前言,说明内容大多虚构,以免被人说是诽谤罢了。
宋:要不就是明知故犯说你诽谤,要不就说你的调查工夫做得一塌糊涂,或根本没做。
冯:所以要核对事实。开始时,只想说清这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岁数。必须先弄清楚,赵四与张学良到底何时相识。问题是,他们事实上何时认识,张爱玲也未必清楚,那便要考查她到底看过什么,怎样处理那些史料,从而找出她的角度。
我考究周四小姐的年龄,不是因为受了红学的影响,专门研究年龄和年份,其实我对此并无兴趣,但因要写这篇自辩文章,才从这古怪的角度入手。但这样写,文章肯定乏味无比,谁会对这些年份有兴趣?
要把这如状书一样的文章稍稍改换,就想到用一个文学批评的包装,另找一更深的角度。考证完了,对我了解文本或者诠释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吗?过程中,我发现有点像福尔摩斯查案一样,自己也好像在写小说,因为正在诠释别人怎样诠释一些事;当你诠释时,你已加入了个人的文学想像,再去诠释那作品,便成了双重想像。就是在一个想像的世界中,再想像另一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最后好像在写侦探小说,只不过是用历史人物做角色,他们有的真实有的虚构,并以文学批评为背景。我到后来才发觉可以写这样的东西出来,觉得有趣,越近尾段越有意识,但开始时并没想过。我在文中也暗示了我正在做这种小说创作 ,不知道其他人能否看出。
郭:找数据方面又如何?
冯:其实很简单,首先要缩窄范围。《少帅》是张爱玲在一九六三年前后写的,你看她之后的书信,本想继续写下去,但没动笔。你可假设,一九六五后出版的所有关于张学良的书都不用理会,然后便可到图书馆找有哪些相关的书是此前出版的,不论中文或英文,都可看看书目,我发觉也不算太多。
然后,再看看她信里有否提过一些宋淇寄给她的书,也不太多,Donald of China一定有,但其他那些我又怎样找回来?就只是碰运气。
郭:我见你在文中找了好些旧日的《春秋》杂志来做考证,过程困难吗?
冯:《春秋》可到中央图书馆看,很齐全。说起来我与《春秋》也有渊源。我几年前到过“春秋杂志社”学古琴,在弥敦道,那时还未帮手做《少帅》的工作。我喜欢那里的旧书,后来看到张爱玲在信中提及有人把《春秋》寄来,便知道是什么。
那年代写民国轶事的书其实有限。你可想像,当时很有名的《春秋》杂志专讲民国轶事,而且海外有分销,如张爱玲想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不可能不读。最初便想,张爱玲是在华盛顿读到,抑或有人寄给她?按推断,应该是有人寄给她的。我看了各期《春秋》的目录,再比对内文,发现张爱玲有不少内容是直接从那里拿过来的,于是可以确定,她也读过那几期。把范围收窄,再随机搜索,当然也有没用的,譬如徐铸成在《金陵旧梦》也写过张学良,但跟《少帅》无关,便没放进文章。
郭:但你是纯粹想知道,张爱玲所用的材料是从哪里来?
冯:否则你怎知道,十三四岁这件事,到底是她虚构,还是取材于其他数据?这很重要。如果是诽谤,你要看看是否有一个版本曾提及赵四十三四岁已认识张学良,并发生关系。我确定是没有的。
没有的话,这明显就是张爱玲虚构。要想她为何要这样虚构,就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了。所以,工作其实不是印证历史和张爱玲的版本,而是印证张爱玲读过的版本和她写的版本,那才有意义。不过我也要知道历史事实是怎样的,这就成了几重工夫。
所以我第一重意思,不过是当自己是历史学家,去看那时候的这段爱情故事,看看能否还原其本来面目。另一重更有意义的工夫,就是看看张爱玲怎样处理她看到的数据。
翻译修订:不学张爱玲,又似张爱玲
郭:翻译的情况如何?
冯:宋生识得郑远涛,他曾来访问。
宋:他那时是张爱玲迷,知道我手上有很多东西,问我可否给他看。他最有兴趣的是张爱玲和她姑姑的书信,我就影印了一些给他。譬如一封说她姑姑在八十年代,第一次想起可以联络张爱玲。以前因为“文革”,很避忌,尤其那属于海外关系。郑远涛后来据此写过一篇文章。后来我知道他在做翻译,译他自己喜欢的书,如《波斯少年》。
开始计划出版《少帅》时已知需要翻译。之前的两本《雷峰塔》和《易经》,张爱玲有厚厚的打字稿留了给我父母,当时认为工程太大,不知怎么办,出版社就在台湾帮我找人去做,效果不算很满意,有时候也让人烦恼。
都是张爱玲衰,因翻译是个台湾人,没法知道香港事,译了出来,看来看去都不妥帖。譬如说,书中女主角在香港大学下山,接着乘电车,电车去的是Shovel Bay。Shovel是铲,他就不懂译,什么是Shovel Bay?最初我也愕然,便做了些蠢事,找找香港到底有多少个Bay。三十个,逐个对,没有一个是Shovel。再想想,发觉自己真笨,你乘电车从坚尼地城出发,在湾仔警署下车,那肯定就是向东行。究竟车头牌上会写什么?可以是湾仔,北角,筲箕湾。“筲箕”这两个字,英文没有,便明白了。我明白译这些难度很高,但也先不要理会,总有人能帮忙。
译本里有其他东西读来不太舒服,不过当时要找翻译也困难。现在译《雷峰塔》和《易经》的赵丕慧其实已是第二个。第一个是张爱玲迷,熟知其事,但第一本未译完就投降,为什么呢?张爱玲上了身。她变成了书里面的张爱玲,父母想跟她沟通也不行,哈哈。
郭:那么恐怖?
宋:这是真的。
冯:怎么没听你说过?之前听过你说类似的版本,但“上身”好像不过是个比喻。
郭:关于这也可以写一部小说。
冯:这一定要写,我从未听过。
宋:赵丕慧是第二个。不同的是她不熟悉张爱玲,为此找了很多张爱玲的书来读,然后才开始。到了《少帅》,我认为这不是办法,不如找郑远涛试试。
郭:那现在郑远涛译《少帅》更似张爱玲吗?
冯:没特别说似不似,因学一学还麻烦。我研究过张爱玲怎样写,发觉如你学她,别人随时以为你错。她用的中文有时反而不太好,你看她英译中那些作品,特别易看出问题。不过那些问题不重要,只是有点怪而已。张爱玲写就没问题,因那是张爱玲,怪也觉得是高手。但如你学她,别人就不觉得你是高手,只觉得你怪。
冯:举个例子,我们商量了很久:“She herself had been in love a long time.”你会怎么译?
郭:“她早就恋爱了”?
冯:但意思就变成她正在拍拖了,但文中的她是没拍过拖的。我们最初讨论时说,如这样译,便分不出她拍过拖没有。郑远涛也说,当张爱玲写“恋爱”时,只在有对象时才用,故这样就译不出原句的意思,因这是她单方面幻想出来的。还可怎样译?翻译就曾说“她自己早就爱上了”。
郭:不是更需要对象?
冯:对,故又有“她自己早就爱着了”,但都不好。然后说到,“fall in love”不就是“堕入爱河”?但那是张爱玲会写的吗?
郭:但英文又不太像,只是 “in love”。
冯:对,故余下来中文可表达的话,便只有“情窦早开”,否则就没法译。不过,我后来发现,以为“堕入爱河”是琼瑶才会写、张爱玲不会用的想法是错的。她用过,你看看,在《色,戒》这里:“这样的女孩子不大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问题是,《少帅》这处可用吗?我又觉得不行,因《少帅》里是一个短句直落,这 “in love”很重要,不宜用“堕入爱河”这种套语去译,会很刺眼,也把这套语放大了。《色,戒》那句意思复杂点,是强调她扺抗力强了,故当张爱玲用套语时,那一定不是句子的重心。如果《少帅》这样译,就很不像张爱玲了。
所以翻译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一句也要反复思量。就算张爱玲自己译也一样难,因她也会受中文的限制,但她可随时把整句改换,你也知道,张爱玲译自己东西时有很多改动,但我们改不得。
郭:结果译了多久?
冯:其实译得很快,约三四个月,不过修订却做了很久。他译完,我校,他再译,我又再校,好像永远也做不完。
宋:结果就要给他们一个限期,不理他们怎么改。
郭:翻译总共改了多少次?
冯:无限次。再举一例。书中周四小姐曾引用成语 “change and die”,表示老帅封大元帅是凶兆 。这成语,你觉得中文是什么?郑远涛问我,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很旧的说法,因他住北京,便叫他问问北京的老人,也找不到。上网google当然也没有。 “change and die”可有几多种变化?“变则死”?“变则亡”?都查不到。
两年后,我在中华书局偶尔看到几本成语辞典,收录了不少旧日的成语,翻了翻,查到一句:“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就是这句吗?好像不似,但想了想,正因不似才一直找不到,似反而早就找到了。相差真很远吗?你想想,把这八字译作英文会是什么?“不死则亡”不就是die, “变古乱常”可译得长些,但就不能和die对称了,故很可能简译作change,略去的意思也不多,因“变”和“乱”相近。郑远涛听后觉得太文绉绉,但成语不少都如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也很文雅?虽然最终仍不肯定,但这句好像最似,无论如何比“变则死”好,因那是没根据的。
修订翻译的同时,又发现张爱玲用了很多西方典故和双关语,这些如何处理好呢?我便尝试将它们融入到我那篇考证文章中。一边校读译文,一边对小说有更深的看法,便再修改我的文章,然后又对原文有更深的看法,如是者一路改下去,愈写愈长,很多想法最后都要浓缩成文章后的附注。
英文写作:不想做另一个林语堂
郭:看《少帅》时发现,不少地方跟张爱玲其他小说重复,似乎她有很多东西储了下来,然后中文英文转换地写出来。
宋:她有些很喜欢的句子。先写进一本小说,谁知不能出版,或没有写成,接着在下一本,便不择手段一定要用那句,怎知道那本也出不成,哈哈,再下一本总之要塞进去。譬如说她写祖父祖母,“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这句,我查过,她用了四次,以前三次都不能出版。
冯:《少帅》有些句子是从《异乡记》来的,故初时可能是从中文变出来,但有些又再变回《色,戒》的句子,即是中文变英文,英文变中文。
郭:这过程可以横跨十几二十年。
宋:讲个题外话,有些张爱玲的事,纯粹是好运地知道。如她在语录说,有些人在幕后帮手做事,写了八个字:“有口难言,无奇不有”。谁知道在说什么?幸好我在家里见过爸爸有个剧本叫《有口难言》,用笔名写的。还有妈妈翻译过一本英文书,叫《无奇不有》,又是用笔名。张爱玲那句,是说他们二人用笔名,在幕后操纵。
冯:故还有一句 “人在幕后戏中戏 ”,在这八字之前。
宋:那剧本和书我都有,是幸运,外面的张爱玲专家,都不会记得这些。那个“无奇不有”根本无人知道,因为又不是一本好书。但我家里有四本,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自己有份。
郭:刚才说,张爱玲几本背景比《少帅》简单的小说,在国外出版也艰难,故我不明白《少帅》为何还会那么复杂,尤其如第六、七章写军阀混战,美国读者简直不可能明白。她的信心从哪里来呢?何况她还用了那么多时间写。
冯:回到根本问题,她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如果她想写历史小说,会写到人人都明白,像林语堂那种方法。你觉得她真的想别人明白那些事吗?
你要知道,她不喜欢写不真实的东西,她本身就欣赏真实之美,所以想加多一点细节,来保留那个世界的质地。还有,你有否留意书中那些对话,往往无头无尾,她不会先给你背景,故不论谁人在看,都要想究竟在说什么。
郭:但人名真要那么多吗?如文中“方申荃”这些大闲角,跟说有“南边的一位领袖”有何分别?我们都知她想影射谁,但对国外小说读者来说,不会太复杂吗?
冯:问题是,如不写人名,用身份来代替,她会觉得假,是造作牵强的写法,所以她不是从读者的角度入手,考虑的不是易不易明,而是那写法是否恰当;张爱玲虽想和林语堂竞争,却不想做林语堂。如用林语堂的方法而成功,对她来说其实是失败。她在《私语录》也曾说,欣赏林语堂的中文远多于英文。她明显不想做另一个林语堂,虽然她知道那条路会较易成功。
冯:她最欣赏的是《海上花》,几年后就译了出来,介绍给西方读者。她知道《海上花》不会很多人欣赏,只是觉得西方批评家多,总会有几个人知道她想做什么,便够了。《海上花》贴近她的美学观,一众角色荡来荡去,那么多人名,就算中国人看也会头晕眼花。
回到《少帅》,有些地方根本不是接着前面的事情来说,很难懂。这样处理是为了什么?其实她在告诉你:这些不是读者需要知道的事情。她想你代入周四小姐,听旁人的话时,就只觉得不可理喻。如要切实反映周四小姐的内心世界和处境,正需要这种方法,要令人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所以张爱玲这样写,其实是刻意的。她不想太过火,令人抗拒,故也把无谓的东西简化,不过始终有底线。
张爱玲用一些很细致的工笔来描画,但画什么呢,就是背景。譬如说现在有两个人对话,她会把后面的东西画得仔细,这也是《红楼梦》的做法。后面画得仔细,不是想你去注意,不过希望给你一个背景,去烘托前面的事情。背景马虎,前面的事情就不能烘托出来。你说那些军阀的事如此繁复,就可说出周四小姐当时身处怎样的处境,会觉得多茫然──身旁的人都像一群红母牛一样,在做些古怪的仪式。书中就有这比喻。
张爱玲不断强化这感觉,才有那种细致的描述。我想对她来说,国外读者能明白她的用意已经足够,无须把历史背景都考究出来,因这样读小说是很没意思的。
历史小说:实则是想建构一个世界出来
郭:那你们觉得《少帅》好看吗?
宋:问题在于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有人给你这本小说,不告诉你作者是谁,你读来会很疑惑。但如告诉你这是张爱玲写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尤其是如你熟悉她,就会开始想其他问题,不只看小说本身,而会问她为何要用历史人物做主角,这是她从未试过的,故《少帅》是否好看,很视乎你的角度。从她本人小说史的角度来看,《少帅》比《雷峰塔》有趣得多。
冯:我也觉得如此,《少帅》比《雷峰塔》写得好多了。我比较喜欢她七十年代那四篇,觉得比她在上海所谓那黄金两年好得多,不论技法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也肯定高于《金锁记》。有朋友说《色,戒》最接近“神”的境界,我很同意,李安拍的根本是两回事。我最近又重看《色,戒》,因要写篇文章比对其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译本,故要逐字去读,感觉跟先前很不一样。她后期的著作如《相见欢》,多看几次,便知道她的写法,明白为何都不受欢迎。张爱玲已不再是想着出名,因那时她早已成了名。她初期写的才多玩文字游戏和金句,就像王家卫拍《一代宗师》,洒一堆金句,要你征引要你记住。张爱玲的早期作品无甚深度,都靠比喻、机智、文采去吸引你,这她都做得一流,如王尔德一样,水银泻地,所以立即出名。
但这是不持久的,不会因重看而加深理解。但她后期的作品,却会因重读而发现新的层次,如《色,戒》就是她中短篇中最好的,跟她原初用英文写的 “The Spyring”已不一样,虽说有些特务的情节是宋淇给她的,但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正如《少帅》中讲张学良那些都非重点。重点是她如何处理材料,如何在上面加添自己的颜色,而效果总是含蓄,不着痕迹。是我想得太多吗?不可能,你看她后来写《小团圆》,以她一个这样聪明的人,你觉得会愈写愈差吗?
她只是在玩另一游戏,将先前的游戏规则统统改掉了,但改完却不告诉你,明明白白告诉你就没意思了。很多人就觉得她已江郎才尽了。
郭:有趣。
冯:从《少帅》开始这时期便是如此,初看会觉得平淡,不知她想做什么,是未修订好吗?但我曾刻意给一些女性朋友看,她们看完都觉得感动,不是因为历史人物,那都可以跳过不看;而是为小说描写女子初夜的段落而感动,觉得有共鸣,能反映她们的心态,有些人还说边看边哭,男性读来当然会很不同。
张爱玲觉得这最值得写,她在信中也讲明《少帅》只是个 “framework”,我觉得她要借此框架说的,就是她的初夜。为何《少帅》用英文写?你想想,不用英文很尴尬,如你是张爱玲,你也不会用中文写初夜吧。就算讲明不是她自己,读者也会这样猜,所以不会够胆用中文。我觉得《少帅》就像缓冲,好预备用中文写《小团圆》,才先用外语,跟不熟悉她的异乡读者表露自己真实的一面,写最震撼她的经验,而且那一定是真的--“用外语讲真心话是特别真的。”你知这句是谁说的吗?是黄子华。
所以我觉得她是想着自己,却包装成一历史小说,重心则明显是写她的初夜,讲女人的命运,后来到知道《少帅》出版不成,才写《小团圆》,故你看《小团圆》写床上戏许多跟《少帅》相像。以前她很少写这些东西,《少帅》和《小团圆》却都写得露骨。
郭:对。
冯:回到好不好看的问题。我的角度是这样的:好不好看,视乎你怎样看。为何张爱玲在国际文坛的地位不高呢?那就要问,有多少外国学者会花大量时间读她的书。如不花工夫看,或没那些背景或知识,根本看不到细节,不会明白她想做什么。不能正确地欣赏她,就没法正确地评价她。
我甚至觉得,夏志清对《少帅》这些作品的评价可能也不高,因为他也未必会投入很多精神去读。张爱玲花了大量工夫在细节,如不花同样的工夫去读,便难理解。正如我给你一首Horace(贺拉斯)的古罗马诗, 因你不懂拉丁文,看不到他的文字游戏,读英译只会觉得无聊,连说十行都单讲饮酒。若你知道原文如何,他怎样处理双关语,调节音乐和节奏,整首诗便全不一样,所以都要看细节。
张爱玲的作品翻译后也是另一回事。中国读者如只追看故事,也不会觉得好。但如你认真看,会发现她很多东西都是故意的。发现了她的意图,便会觉得写得好。跟四十年代不同,她已不想用金句去干扰你了,只想你慢慢看。如你看不明,我觉得她是心甘情愿付出那代价的,不过她相信总有人会用心逐字逐字去看,虽然只是少数。
不是要写那篇考证文章,我对《少帅》也不会感兴趣。但写下去,将所有细节研究了出来,便觉得很有趣味。所谓好不好看,通常是指学界最有地位的人觉得如何,一般人见学者说好便容易说好。那些学者为何会觉得好看呢?因为他们专门研究这东西,看得仔细。但有些作品本身是耐不住你去细看的。要在强光照射下还能抵受,而你能看出细节和纹理,才算好。从这角度,《少帅》写得好。但如不用强光照,便是模糊一片,所以也注定大部分人会觉得不好看。也可以说,张爱玲其实在考验你的耐性,要么不看,要么就花时间看。
反问你呢,读完觉得有意思吗?
郭:有一点觉得有趣,关于变与复不变,好像不是“现在”取代了“古老”,而是古老根本从没离开,只是反反复复如潮涨潮退,有几处刻意将这古今并置,如写到革命党已拿着土枪土炮了,一个军阀用的还是大刀队,结果大刀队都不敢下火车。又或写北京城那守夜的钟楼时,就提及新式时钟,两者在小说同时出现。男女的身分也一样,书中女人的身份都是对应于男性的,不是妻子妾侍就是妓女,而男性的分类则是职级和成败。到了现代,在革命之后仍是如此,分毫没改变过。
另外有一依稀的印象,就是觉得《少帅》跟《色,戒》相似,有点“两般疑幻又疑真”,而且都跟演戏有关,好像试图寻找真实。
冯:但张爱玲似乎在说,很多真实,不过是你以为是真,而主角心底都知道不是真的。就如《色,戒》,王佳芝从珠宝店出来后,街上的人都像隔在玻璃之后,如同橱窗里的模特儿,行人甚至路过的车,对她来说都不是真实的。《少帅》也暗示了写的都不真实,如少帅揽着周四时,周四便想,因为二人年龄上的差别,好像属于两个朝代的人,觉得少帅像是书中人,于是就可很勇敢去爱他;反而害怕少帅不明白,以为自己真的喜欢他,以为她真那样够胆和shameless。正因她觉得自己身处戏中,才如此放肆,但做出来又像在真实世界,我觉得便如double simulation,双重的模拟。就如一个密室中,有一个人在行来行去,他跟自己说自己是疯的,然后便如疯子一样行动。过了一会,他就再跟自己说,我痊愈了,变回正常。那他真是变回正常吗?还是装疯的人扮正常?这是无可救药的,很绝望,因表面上正常,但心底里却是装疯子再去扮正常,我觉得张爱玲写的也是如此,主角觉得那些东西假,但都装作他们都是真的,继而又自觉那些仿真的事物很像虚构 ,那 “as if”因此是两重的,很多东西因而都一层层走不出来。
《少帅》到最后也在把玩这点。如说到那英国人,想做海关骗钱却给少帅赶走,很快就因分赃纠纷而给杀掉。周四小姐知道了立刻说,那是少帅最威武的一刻,之前中原大战死了三十万人,也只是如梦如幻,直至少帅在罗纳面前赢了这洋人,才觉得最真实。那比喻简真是金句:仿佛一场枕头大战,线头裂开,飘了些云雾出来。但写下去却笔锋一转,从真实的事,回到了这死去的英国人写的第一本书,讲的正是拳乱和抢掠,想不到他三十年后正正死在其中,所以一下子又像回到了书中,由真实返回虚假的世界,那书就像预兆。因此是由真去假,又由假去真再去假,不断来回,令读者和周四都分不清孰真孰假,或孰新孰旧。
郭:对。
冯:所以说,她也不是要找真实的东西,而是想建构一世界出来,像《色,戒》,我觉得像神的境界,因为那近乎一些 gnostic 的想法,觉得这世界是个神自己幻想出来的。《色,戒》所有东西都是王芝佳自己想出来的,完全像没发生过,但幻想出来的东西却可有很大影响。
这也是《少帅》的情况。一开始,无端有人抛些东西上洋台,便很假;到最后,写少帅带着两个老婆下飞机,说新中国已出现了,迎接新世纪,也很假。《少帅》从头到尾,其实都在强调假而又像真这命题,历史人物反为次要,却有助烘托主题。张爱玲是一路收起这主题的,因为待你揭开几层,自己发现,你才会觉得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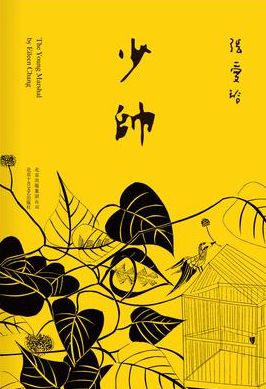
少帅
英文书名:The Young Marshal
作者: 张爱玲
译者: 郑远涛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