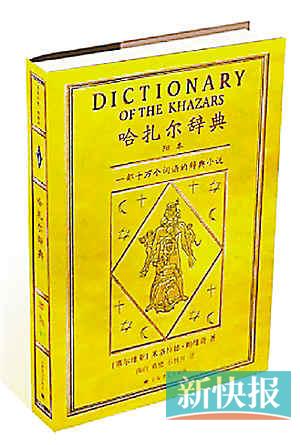
(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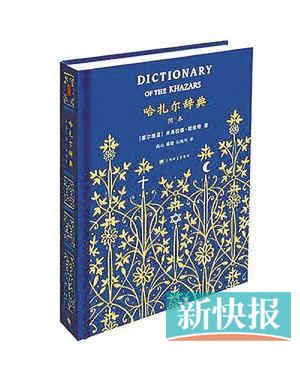
(阴本)
《哈扎尔辞典》时隔15年再版
作为20世纪的作家,却写出一部被誉为“21世纪的第一部小说”——还有什么比这个评价更令作者帕维奇感到得意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成功地避免了陈旧的阅读方式,也就是从传统的开头读到传统的结尾的方式”,他说。就像本书副题“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所揭示的,《哈扎尔辞典》独特的叙事方式,是它被称为奇书的最重要原因。
时隔15年,《哈扎尔辞典》(阳本)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度出版,并将于今年10月推出限量豪华版《哈扎尔辞典》(阴本)。
●米洛拉德·帕维奇(1929-2009)塞尔维亚作家,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代表作《哈扎尔辞典》开创了辞典小说的先河。其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铁幕》(1973)、《青铜器》(1979)、《用茶水画成的风景画》(1988年获南斯拉夫最佳作品奖)、《风的内侧》(1991)、《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1995)、《鱼鳞帽——艳史》(1996)。
●《哈扎尔辞典》阴阳本之谜:
11行,找不同
《哈扎尔辞典》自问世以来,就有阴阳本之分,但阴阳本究竟有何不同,作者并没有说明。据介绍,阴本和阳本(中文版)只有11行字不同,但又从来没有谁能说清楚这11行不同究竟在书的哪个位置。对于这个谜,本书中文译者之一南山的解读是,“帕维奇这样做,第一是对流传下来的哈扎尔文化或者历史传奇的传承和尊重;另外,帕维奇创作上有一个观点,他永远认为读者比作者更聪明,他留下这些东西,每一个读者读的时候,你的知识结构、个人感觉不一样,学术观点不一样,你读到的观点不一样,从而开放阅读套路给读者,供读者自己解读”。
●限量豪华版:阴本
此次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出版的阳本已于今年年初面世,短短几个月已重印数次,而阴本限量豪华版也在制作当中,预计10月份上市。与阳本不同的是,《哈扎尔辞典》阴本只印一次,装帧是中文图书市场上罕见的皮面竹节(书脊)精装,书脊上镶有限量红宝石。
“娘们儿没有肥臀,就像村庄没有教堂。”
切勿抱定这是本难读的书而避之不及,尽管它眩人眼目,故设迷局。下面是我初次邂逅《哈扎尔辞典》的场景。去年夏天,在意大利一处开销低廉的海滨,我住在最好的酒店里,缘由就不表了。海滩上一把阳伞下有一位热情的法国商人和他妻子,她是从约克郡搭船来的。(“三十五年前我正穿行过巴黎,如今我依然在穿行。”)他刚做完心脏血管绕道手术,正在康复;他的胸口涂了防晒油,胸毛结得一团团。这对夫妇最初引起我注意是在酒店餐厅,因为他们点任何东西都要浇酒火烧。她,穿一条印着巨大橙色花朵的紧身连衫裤,在沙滩上同我的小儿子跳舞。当时她丈夫就在读《哈扎尔辞典》。书刚在法国出版,是他的假期读物。他总是大声地念一点给她听:“阿勃拉姆老爱说一句戏语:‘娘们儿没有肥臀,就像村庄没有教堂。’”“那我还行。”她说。他开怀大笑,我真怕他伤口崩裂。吃晚饭时,他就趁服务员往牛排上浇酒的当儿,为他读上几段。
我想要是这对可爱的男女这么喜欢读这本书,那我也会的。其实,或许对付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声地念几段,像玩游戏一般。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罗伯特·库弗写道,如果此书被改编成桌面游戏推向市场,也许很快就能比“龙与地下城”更畅销,没准儿是真的。这是本游戏之书,打开来取出东西,宝盒里装着乐趣与把戏。这是部与终结感绝缘的小说,丰沛无垠的想象力的结晶——称得上是“方便用户的”,邀你自行创作。
(安吉拉·卡特/文顾真/译原文载于《伦敦书评》)

“这一刀若刺中,溅出的鲜血会发出人的喧哗声。”
帕维奇的小说语言是奇特而有生命的,但是除此之外,鉴于《哈扎尔辞典》所涉及的历史与神话传说内容,小说的叙述语言更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绚丽气质和魔幻色彩。读者翻阅这本小说,会发现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而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语言,则常被用来描写声音、颜色和味觉。
在谈及阿维尔基·斯基拉(17世纪末君士坦丁堡最著名的刀术师)已臻完美的刀法时,作者写道:“这一刀若刺中,会在对手身上留下一个蛇形大伤口,溅出的鲜血会发出人的喧哗声。”这当然不是写实之语,谈论它真实与否也全无意义,我们只需留心作者对声音的把握及其所达到的传奇效果。
再来看颜色:“当时正好三面来风:从黑海刮来的风是绿油油的,从爱琴海刮来的蓝得透明,从伊奥尼亚海刮来的则干燥而苦涩。”风是无形无状的,也没有颜色味道,但是地域是有文化的,人是有思想情感的,这正是帕维奇描写的根据之所在。
同一道理,帕维奇以同样的方式来写味道:“匈牙利人转过身子正想回他发散着红辣椒味儿的里屋……他把这话悄声译成匈牙利语。显然,他只能用他的本民族语来记数,从而一种奇怪的气息在房里弥漫开来。那是甜樱桃味儿。我明白了:这味与他的心情改变有关………他刷一下披上大衣,店堂里立时发散出樟脑味。”这样的处理当然非常奇特,甚至怪异,但是以帕维奇的思路来看,也能够言之成理,并达到其语言效果。
(alabozhiye/文原文题为“词句已成血肉”)
“那边不流通我们的货币,连我们的观念也分文不值。”
“在每一个梦的梦底,都非常非常深地深藏着做梦人的死亡。因此深沉的梦,我们一醒过来,就忘得干干净净,这是因为人的过去与未来都活于神秘之中。两者一离开神秘,不管怎样都必死亡。我们的未来,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异邦语言。未来乃是有待我们去开拓的广袤的大陆。也许,未来就像是大西洲。那边不流通我们的货币,连我们的观念也分文不值。”(《鱼鳞帽──艳史》)
我觉得,这段话也可以代表作者自己体现在《哈扎尔辞典》和这类作品中的梦想的诗学,他的心灵在看待生命和世界时,保持了神秘感,即世界和生命不可穷尽,也不可能为理智所捕捉。他从人类世代的语言文化积累中重现发掘其神秘因素,并赖以进入历史、宗教、语言中未被表达以及难于表达的世界。
(艾晓明/文原题为“寻梦者的疆土”)
帕维奇访谈录
“作为一名作家,我出生于二百年前”
拉莱斯(下简称拉):您对世事的反应就像一个小孩。您给我的印象好像您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塞尔维亚作家似的。
米洛拉德·帕维奇(下简称帕):事实上我正是这么觉得的,我尝试用初见人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为了能继续生活和写作,我尝试忘掉所有我写过的书。
拉:开头和结尾肯定是小说家最大的麻烦。
帕:我已尽我所能去清除或毁掉我的小说中的单一的开头和结尾。至于《哈扎尔辞典》,你想从哪儿开始阅读都可以。但是在写作它的时候,你不得不将书中哪个条目先于或接在另一个条目之后牢记在心。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成功地避免了陈旧的阅读方式,也就是从传统的开头读到传统的结尾的方式。
拉:幻象是不是人们用来与生活的“事实”相抗争的武器?
帕:作为一个作家,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当真认为,一个作家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才能便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即现实与幻象对他而言其实是同一个世界。惟其如此,事物才会以其应有方式正常发展。
拉:在您看来,创作最佳作品的真谛是什么呢?帕:我相信,只要你的恐惧达到了最大极限,最佳作品就会出现。我们离自己害怕的东西越近,也就越朝最佳作品迈近了,恐惧将把我们引向超常,真正的超常。正是在这里人们才会找到真谛。
拉:艺术中美的标准可能就是自然美吗?
帕:没有一件艺术品够格来描述自然美,不过艺术美是自然美的一部分。
拉:对您而言艺术美的真正涵义是什么呢?
帕:站在排水沟里的一只长腿鸟,为了不致沉下去,它得不停地活动。假如艺术停止其活动,即使只是一会儿,它也会沉沦下去。
拉:您是否已经找到了无论干什么都可以令自己很突出的秘诀?
帕:首先是毅力。
拉:您认为伟大的作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
帕:作为一名作家,我出生于二百年前。你也知道,在欧洲最大的图书馆里人们可以找到我的祖先写的书。每当我开始写点什么,给予我支持的正是我的祖先。我甚至用古语写过几首诗献给他们,以便他们能懂得我。
(节选自《米洛拉德·帕维奇访谈录》塔纳西斯·拉莱斯/文周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