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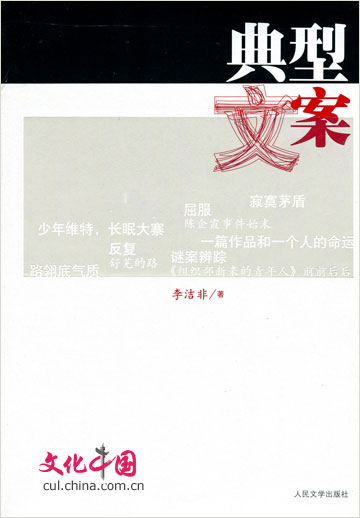
这是一部描述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名案例的研究著作。具有非常扎实的案头功夫和探幽索微、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
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紧紧捆绑,制度力量非常强大,写什么和怎样写都取决于文艺政策和部署。当代文艺面对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物:体制、政策、形势、运动等等。过去研究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其自身原因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因此当代文学史不是一部缘创作而延续的历史,而是一部随时被它外部的强大社会现实因素所牵制、影响和操纵的历史。从特殊性言,当代文学史不是作家史,不是作品史;是事件史、现象史和问题史。因此,《典型文案》和以往对文艺和文艺史的研究都强调主体性,把作家艺术家的才能、性情、修养视为原动力不同;《典型文案》一书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关系”的发微、辨析和阐释上。当代文学史上存在一些集中反映了当时文学境状的典型人物,还有桩桩件件交织着错综关系的文学史案例。分析它们,品味它们的诸多细节,成了《典型文案》主要的内容。这本书,是关于新中国六十年当代文学的一份“档案”。其中,无论对人、事、史,均致力于考辨梳拢,抉微索隐,陈其概要。是一部理路谨严、具有思辨光芒和智慧含量然而又文采斐然的作品。
作者简介
李洁非,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供职。八十年代中期起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后转向专项研究,兼事小说、随笔和史传写作。历年出版著作主要有:《告别古典主义》(1989)、《小说学引论》(1995)、《循环游戏》(1997)、《城市像框》(1999)、《漂泊者手记》(2000)、《龙床》(2006)、《典型文坛》(2008)、《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2010)等。
书摘:王蒙、浩然谈刘绍棠
1956前后,刘绍棠明显地表现出“亢龙”之相。他是如此志满意骄,以至于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加掩饰。我们来看看同时代文坛上两个青年俊杰的描述。
王蒙在其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几处涉及刘绍棠。一处说:
在这个会议(指“青创会”—引注)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表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表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作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
这三个“最常说的词儿”,刘绍棠恐怕是唯一尽得风流之人。“发”得最多,也有“集子”,还已经“入会”。而王蒙当时仅仅“发”过两篇作品,舍此再无资本,相形之下,用他的话说“只有汗颜”。不过,体味王蒙行文,这个“汗颜”与其说是他自己觉得,毋如说是在别人炫耀之下被迫觉得。尽管他只是隐隐约约将刘绍棠的名字轻轻点了一下,但那个“强得多阔得多”、大肆炫耀者的身影,还是跃然纸上。
假如上面那段话,所指尚嫌朦胧,那么翻过一页,人物形象就变得极为鲜明了:
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
这百十来字,是一幅微型肖像画,指名道姓描绘了1956年刘绍棠公开场合的表现。“轻狂”是文眼,“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是其具体表现,对话则是所有这一切的形象化。
那么,是不是王蒙心怀妒意而刻薄为文,致使笔下有所夸大呢?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个人的描述,他便是浩然。从生活文化背景以及创作题材论,浩然、刘绍棠之间的相似性,大于王蒙、刘绍棠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他们彼此的渊源也深得多。所以,浩然对刘绍棠的感受,比王蒙更具参考价值。
据说,早在1951年他们便打过交道。那时,刘绍棠以“十五龄童”已经“发”了十几个短篇,还获过奖,在保定当上了《河北文艺》见习编辑。浩然却在蓟县无望地收获连篇累牍的退稿。这些退稿中,有一篇就来自刘大编辑。《刘绍棠传》说,“按当时规矩,退稿信只能加盖编辑部的公章,不许编辑个人署名”,刘却“因对浩然很有好感”,在退稿信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郑恩波先生把这件事当作浩、刘友谊来写,说“浩然把绍棠的这封信保存了多年,即使在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年月,也没有舍得毁弃。”然而,查《浩然口述自传》,所涉刘绍棠笔墨甚多,关于此信却只字未提;推测起来,纵有此事,它于浩然恐怕也非“温馨”记忆。
若以《浩然口述自传》为据,浩然对刘绍棠的回忆,只有负气和不快。他回忆的起点是1954年,当时,浩然慕刘绍棠之名,托人称刘绍棠“小兄弟”的从维熙牵线,彼此认识一下。丛当即表示不成问题,说大家“都是冀东老乡,你们俩一见面准能成为好朋友”。约好星期天在丛维熙工作单位北京日报社见面。那日,浩然“早早地从通县专区记者组动身”,赶进城来找到北京日报社,在门口左等右等不见人来,眼看是中午,浩然就打听了丛维煕宿舍地址自己去找:
我按照门卫的指点,绕到东边拐进头条胡同口,一边往西走一边查看门牌号码。正在走着查着,忽见从维煕从胡同的对面走来,旁边跟着一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年轻人。那人胖胖的,有点黑,戴着近视眼镜,不用问,他一定就是刘绍棠。我高兴地喊一声“从维煕”,随后大步地迎上前去。从维煕见了我,微微发了一下楞,立刻停住脚步说,你说的事儿让我忘了。他指指身边那个胖乎乎的人介绍说,这就是刘绍棠。我赶紧朝刘绍棠伸出手。刘绍棠看我一眼,伸手跟我握了握,客气地笑笑。从维煕又介绍我说,这是梁浩然,《河北日报》的记者!话未说完,刘绍棠脸上的笑模样像凝住了似的,他打了个难解其意的手势,眼神不再对着我,说他现在很忙,就连中央大报的记者采访,也得事先约定时间,以后有时间约定时间再说吧。话音刚落,他就继续举步前行,不再理睬我了。
说起这一幕,晚年浩然自嘲曰“追星族”,被人家当成“纠缠者”,对刘绍棠则以“名人”相称,说他“正处于‘幼稚可笑’而又自视成熟、很了不起的年龄段”。浩然坦言,后来刘绍棠掉落云端,自己内心很长一段时间都“认同别人对他的批判”,“我尤其认同批判他‘狂妄和个人主义’”。
连王蒙、浩然当时都从刘绍棠那里受了一肚子气,其待人的轻慢、骄矜以及毫不屑于掩饰,可见一斑。
浩然还讲到后来批判会上一个细节:
一个上台批判发言的人是刘绍棠在通县潞河中学的入党介绍人。他揭发说,刘绍棠在中学念那会儿,没成名时称他为“×教师”,有了点名气改称他为“同志”,乃至成名入党了,他口吐狂言“共产党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光荣,如果不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损失!”
未知揭发者属于信口雌黄,抑或言之有据;如果刘绍棠当真讲过那种话,批他一句“口吐狂言”,真不为过。
此时他的“自我膨胀”,还有一个突出例证。就在他占尽风头的首届“青创会”上,他高谈阔论、大放厥词,“攻击文艺界领导”。2007年12月《党史博采》一则史料称:
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 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李永军:《胡耀邦与刘绍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的一次谈话》)
我所阅资料中,都没有具体指出这位“文艺界领导”是谁,不过,在王蒙自传里看见过闪烁其词的一段,那是1957年2月周扬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约见他的情景:
……通过开青年作者会(即“青创会”—引注),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王蒙下笔羚角挂角,很难判断被刘绍棠“攻击”的文艺界领导就是周扬,不过,从胡耀邦重视和为难的程度看,应该不是“一般”的领导。
胡耀邦把刘绍棠叫去“面责”时,还说了一句:“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虽无认真怪罪之意,但刘绍棠之“狂”,着实堪惊。如果再年长十岁,如果人生经验里曾有过一些坎坷,他大概能够避免翌年的厄运。
(摘自李洁非著《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