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西行》

歌德故居内的“北京厅”布置着中国文化元素的墙纸与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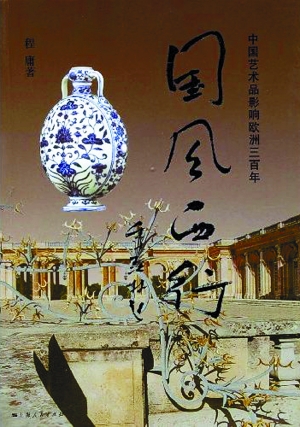
《国风西行: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 作者:程庸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定价:58.00元
“中国风”时代
先讲一个故事:1602年,荷兰远东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强行捕获一艘葡萄牙货船,船上满载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价值300万荷兰盾———这相当于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资本总额的一半,或英国政府支出总额的近三分之二!这种规模的战利品在当时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引起整个欧洲对荷兰人的恐慌和嫉妒。瓷器作为一种精美的艺术品,在令当时西欧贵族倾倒不已的同时,也是他们了解中国文明的主要物质载体,以至于如今英语中China一词仍兼有“中国”和“瓷器”两个含义。
那是欧洲史上弥漫着“中国风”的时代———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瓷器、丝绸、家具、漆器等工艺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有学者估计欧洲仅进口的瓷器数量就达1.4亿件左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而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之大也折射出西方人对中国艺术品的深深迷恋。中国文化的元素由此渗入到西方艺术中去,在洛可可风格中尤其清晰可辨,以至于这种艺术风格有时又被称为“中国装饰”。
瓷器与西方文明进程
《国风西行》所要讲述的正是这段如今已为不少国人遗忘的历史。作者程庸周游欧洲十国,拜访了50多个博物馆和100家古董店,以追寻、探访那个时代的流风遗绪。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早已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而本书就胜在作者的感受都得自实地亲历,并配以丰富的照片,直观地予人以强烈的现场感,也并不故作高深之语,从触发兴趣的角度来说实不失为一本好的入门读物。大概正是看中这一点,一贯重视中外文化交流的季羡林先生才乐于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当然,所有的文化交流中也总是隐含着对抗。虽然现代西方国家时常指责中国人仿制他们的产品,但历史上这种知识产权观念和技术抄袭实际上都起源于西欧。正如本书中指出的,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有一些人实际上充当了技术间谍的角色,他们在中国刺探瓷器的生产流程,期望通过了解和以神秘技术而摆脱对中国瓷器的依赖。第一个描绘中国青花瓷生产流程的欧洲人就是一个16世纪的葡萄牙传教士。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生产瓷器的国家,处于技术垄断地位,但这终于被欧洲人打破。
今年正是第一件欧洲瓷器烧出的300周年———1709年德国化学家波特格尔用七种矿物混合烧出白色透明的容器,他也因此被后世称为“欧洲瓷器之父”,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因怕这一秘方外泄,他立刻就被当地王公软禁了起来。
瓷器的使用是欧洲人餐桌上的一次革命。早期欧洲餐具大多只是相当粗陋的陶器,17世纪时瓷器、刀叉等仍是具有相当社会声望值的奢侈品,许多欧洲贵族世家中瓷器摔坏了还要用钉子拼接好继续使用。瓷器与金银或陶土制成的器具相比,都有着明显的优点,不但数量大,且不腐蚀、不渗漏、质量轻,只要一擦洗又亮洁如新。随着中国瓷器如潮水般的涌入和欧洲本地瓷器的生产规模化,到19世纪,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用上了瓷器。在这个过程中,餐桌礼仪也配套发展起来,这是西方文明史上极为重要的“文明的进程”。
文化传播的“心态”
这当然是值得国人骄傲的一段历史,作者也不讳言他之所以致力于此是为了“想从辉煌的昔日寻找一种力量”以克服当今的一些崇洋媚外现象,来“建立正常文化交流的判断”。
在作者看来,中国艺术品在欧洲受推崇折射出“当时的中国具有世界一流文明的强国姿态”,而瓷器在餐桌上的彻底胜利也是因为“瓷器所体现出来的先进性、科技性”。这些固然不无道理,但却不宜强调过甚。
实际上,从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看,对异文化的迷恋常常并不是因为承认这一文化高于自己。如哈德良统治的罗马帝国一度埃及风格极为时尚,但当时埃及早已被罗马所征服。同样,乾隆皇帝在圆明园里建造的大水法、西洋楼都是欧洲风格,但众所周知,乾隆对英国使节照样视为远渡重洋前来朝拜的蛮夷,他并不因为享受了西洋的异域情调就认为欧洲文明高于中国。20世纪欧洲美术注重从非洲原始艺术中汲取灵感,难道这可以作为非洲国家具有一流文明的证据吗?
试图寻找祖先昔日的辉煌,表面上看是为了重获自尊和自信,本质上却仍是植根于一种自卑的逻辑。(□书评人 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