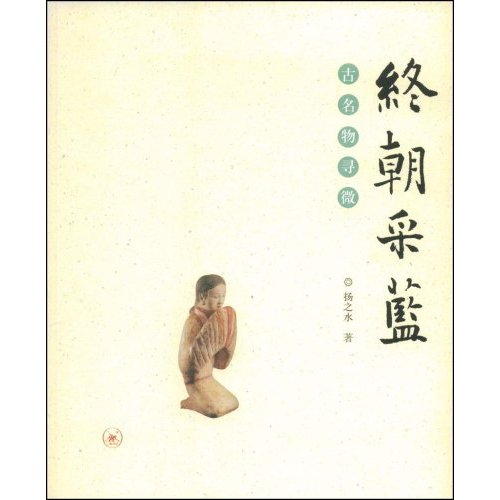
对于一个平常的读者,读《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非要有点浪漫情怀,也许还要有点风雅的兴致,而“古名物”这一名词看上去学术味颇浓,但是往通俗里说,其实大体上就是古人日常物用的别称,这些物事随着时光的流逝或有演变,或者已及身而绝,所以特别需要一份追念的温情才能体味真切。虽然作者的写作是学术的,但笔致流丽意态安详,虽是考证,却弥漫着诗的意境。作者从浩繁的古典诗文里寻绎当时文人对器物的描述与刻画,并穿过迷人的清词丽句,证之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人留存的各类文物,指给我们一个情趣盎然、生气勃勃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作者用语言和图像混搭出来的别致的世界里,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渐次展开。于是前人创造的物质世界所映射的锦绣文明观照眼前,让今人“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遥想不已。
书里的篇什,未必顺序而读,我所感兴趣的乃是那些在今天的生活里依然可见的事物,譬如“宋代花瓶”。作者是从“瓶花史与家具史适逢其时的碰和”着眼的,我们却可以看到其中异域文化交流的缩影。我们从书里知道,花瓶作为室内陈设和几案清玩本是因礼佛的香花供养成就的。所以,我们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所谓专门插花的“瓶”,古已有之的水器、食器、礼器都可以用作盛花的“家伙”,从那些后世出土的唐初的“罂”,可以看出最初花瓶的样子,大约就是“罂”这种“大腹小口”的实用器具的“微缩版”,然后才出现“长颈瓶”的“美学”演进。至北宋一朝,随着桌、案的发达,花瓶独立为专门的设计、制造与用途。既与文房清玩相得益彰,花与花瓶也自韵致相谐。“小瓶春色一枝斜”,花与花瓶皆是案头清供,同具观赏的价值。至此,花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妆点。而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鲜花插瓶不是中土固有的习俗,它与佛教相依在中土传播,走了很远的路,从魏晋直到南北朝,从西域一直到中原,到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