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中学时读了你的《饥饿的女儿》。”这是虹影在成都三场见面会上,多数提问的读者拿起话筒的开场白。
近一百年来的华人女作家,前有张爱玲,后有虹影。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以某种方式外在于传统作家的身份,从而很难被纳入当下文学史;同时她们写作的内容,却又最揪心地内在于最中国的生活,从而不应该被将来的文学史遗忘。
虹影代表作品的集结再出发。4月8日、9日,虹影现身成都,携手梁平、洁尘、何小竹等四川文化圈多位好友一起,与读者深入交流,畅谈自己这么多来在外漂泊的生活、创作的心路历程,畅谈文学与女性、与生活、与世界的关系。
虹影代表作集结再出发
因为不能被将来的文学史遗忘,虹影的写作便始终在国内出版人惦记下。2000年,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饥饿的女儿》,在四川文艺出版社首次面市。去年(2015),虹影遇到四川文艺出版社新任社长吴鸿先生,吴先生谈了读这本书的感想,让虹影心有戚戚焉,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个15周年纪念版的问世,也有了《好儿女花》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首次结缘。
16年过去,《饥饿的女儿》已拥有全球29种语言的译本,累计销量五百万册。如今回到出发地四川文艺出版社,在这里和它的续篇《好儿女花》团圆,加上最新中短篇小说集《你照亮了我的世界》,一个虹影作品的规模集结扑面而来。她的另一代表作《上海王》最新修订珍藏版也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由余男、胡军主演,即将于六月上映。同时,她的首部儿童奇幻小说《米米朵拉》,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市。可以想见,2016年将是虹影的丰收之年。
此次《饥饿的女儿》15周年全新修订珍藏版,由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著名文学评论家费勇、著名文化批评家沈睿作序推荐。《好儿女花》修订近三百处,是虹影精心打磨下的完美版本。
黄发垂髫,共读虹影
4月8日晚上7点,成都太古里方所书店。离对谈活动还有二十五分钟,现场读者区,五六十个小板凳已满,且以中青年女性居多。一位满头银丝满脸安详满身素淡的老奶奶,坐在最后一排。老奶奶告诉笔者,她已年近七旬,家就在附近,今天信步至此,就碰到了虹影的读者见面活动。她说,书中故事的年代,她经历过,见证过,“虹影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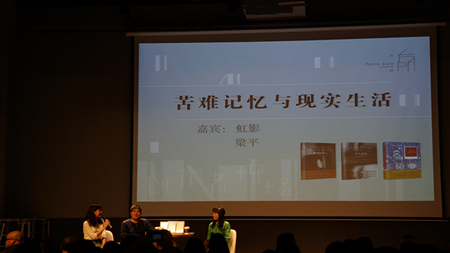
人群中,三个套着大一号白色校服的小女生,略带迷惘和稚气望着台上,不时互相细语。她们是成都三中的高二学生,其中一位说,前几天刚刚看完《饥饿的女儿》,从虹影微博得知了今天这场活动。“书中哪一点吸引你?看完什么感受?”她想了想,认真地说:“真实吧。”
签售环节,排队长龙中一位高个帅气的小男生,捧着一摞虹影作品,粗看共有二十五六本。他是川师的研二学生,专业是地理学,今天肩负着外地网友和学校同学的重托,来找作者签名。
4月9日下午,新华文轩成都购书中心。读者区后排一位戴着眼镜的老爷爷,手上捧着一本200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饥饿的女儿》。老爷爷今年已74岁,今天特地从郊县龙泉赶来市中心参加这场活动。他说:“从2000年这版开始,我就一直购买虹影的书,现在家里已经有十几本。”为什么对虹影的书这么钟爱?“因为她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感受,说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不能说、无处可说的话。”
成都像上海,重庆像北京
在与好友的对谈中,成都与重庆的双城记,是一个频繁涉及的话题。虹影说“重庆男人的鞋子,甚至重庆女人的鞋子,很少有干净的。因为那个地方下雨,我今天是在雨中坐着高铁从重庆来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垃圾,这个地方的人几句话不对挥拳就上来,刀子就拿出来了。这跟成都不一样。成都有点儿像上海,重庆有点儿像北京。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又脏、又瓷、又火爆的重庆的性格里面长大的,这个性格是在我的骨子里面的,我有些书写的勇气,很多写作者不具备,与重庆人的气质很吻合。”
“成都阴柔,有历史底蕴,冲击力和爆发力相对比较温吞;重庆火辣,强悍,带劲。”虹影特别感谢成都购书中心,因为她最初来成都,在购书中心,才知道原来成都的读者这么喜欢《好儿女花》,当时住在锦江宾馆,有读者去把住宿费悄悄代她付了,还给她送金项链。不过,虹影也多次强调,她的写作并不特别强调地域性,《饥饿的女儿》不仅写重庆,也写的整个四川(虹影一直把自己当四川人),不仅写的四川,也写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再后来,她可以写二战后的英国,写印度,写大上海。
“我真的是很多人转世的一个人。当年死了那么多人,却没有一本书讲个故事。所以我是讲述人,是那些饿死的人的代言人,上天选中了我。”虹影对自己的讲述职责给出这样的回应。
张爱玲不依赖男人,萧红总是找错男人
洁尘在对谈中感慨虹影讲故事的天赋惊人。“身为同行,看虹影的作品,不是看故事,而是看文字,呼吸,结构,在这些方面,虹影的天赋是惊人的。”虹影让洁尘想到萧红,两人作品中透出的那股元气,是相通的。
虹影则认为,萧红比较幸运的是遇到了鲁迅,当时的中国没有《生死场》那样的作品,在鲁迅的授意或暗示下,萧红才写出了《生死场》。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就是与世界的关系,因为男人就是女人的世界。但是萧红总是找错男人,把自己生活搞得乱七八糟。张爱玲则比较自我,不依赖男人,不过,1951、1952年离开母语写作的土壤,张爱玲就枯萎了。
《饥饿的女儿》是作为女儿写母亲,《好儿女花》是作为母亲写母亲
有读者问道,《饥饿的女儿》中的母亲形象和《好儿女花》中的母亲形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差别?虹影说,《饥饿的女儿》是我作为女儿的时候在写母亲,《好儿女花》则是我作为母亲的时候在写母亲。只有做了母亲,才懂得体会身为母亲的艰难。
正如她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四川人,讲普通话固执地带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发着一pei(批)快luo(乐)的吐词,在对谈和与读者的交流中,虹影从不回避什么,总是直面问题本身,就像她的作品,也像这个人。

有人在《饥饿的女儿》中看到太多的苦难和冲突,然而阿来却读出了“通过这种人类伟大的情感达成的宽恕”。有人在《好儿女花》中看到了难堪,但沈睿说《好儿女花》“是虹影给世界的自白,独语自白,坦率地谈出一切,好像谁在命令她交出她的所有秘密,她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在世界面前暴露一切。”虹影所描写的重庆,那里的市民却推举她为城市形象大使,这意味着,虹影的写作,真正打到了重庆人的心里,把重庆人意中有语中无的情感体验充分展示给了世人。
虹影说:“1996年第一次在台湾出版《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2009年末,我出版了续篇《好儿女花》,写母亲和我自己内心那些长年堆积的黑暗和爱。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女儿。其实写给母亲的书,何尝不也是给我的女儿。”《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是分别作为女儿和母亲来写母亲,同时也献给了她的母亲和女儿,从这两本书中,我们看到了母亲和女儿交织出的绳索,不是捆缚,而是提拉着虹影,一步步攀登她的写作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