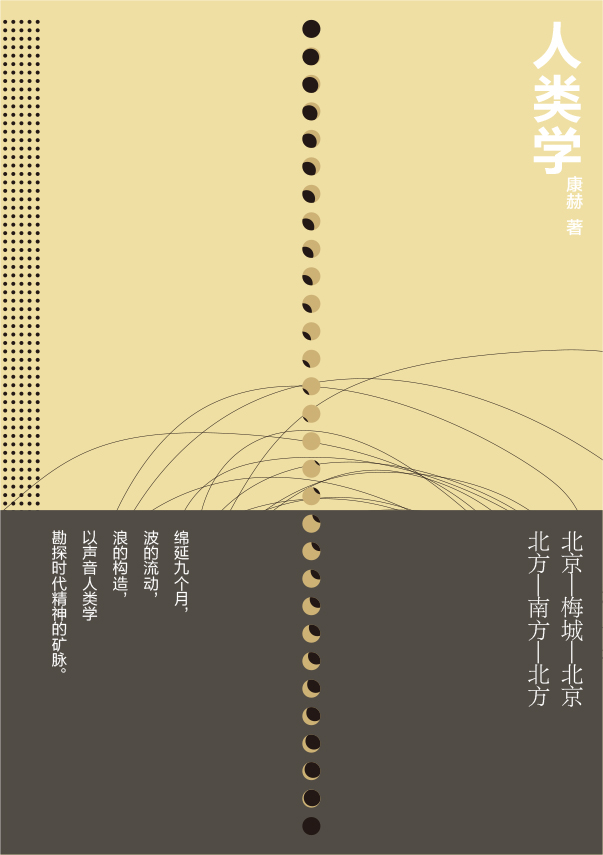
本文为康赫2015年5月在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真人图书“活动上的演讲
反讽是一种神圣的疯狂,像帖木儿一样肆无忌惮
每个人作为一本书,都是另外一些书籍的回声。但是有些人没有回声,他是天才,没有任何来历,爆发,消失,然则严格来说,他其实是天空的回声。老天爷给他天分、才华,他反馈了这样的声音。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天才,老天爷没有给我那么多的才华。我只在我热爱的声音里去辨别,掌握,理解,我是这样一个声音的中介,把声音反馈出去。我是先人的声音的一个回响。要理解《人类学》这本书,其中哪些声音在我身上产生回响,我是怎么处理它的?那就要理清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产生的。你要了解一个单词,就要把它放到一个句子里了解;你要了解一个句子,就要把它放到一个段落里了解;你要了解一个段落,就要把它放到一篇文章里了解;你要了解一篇文章,兴许就要把它放到整本书里了解。
影响我的声音那么多,我只能抽取其中的一条线来说,第一个就是卡夫卡,卡夫卡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回声,“卡—夫—卡”,首尾呼应,自足自在。但卡夫卡的自我感受特别不幸,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古典作家,自认为是个没有完成写作任务的人,但追捧他的则都是后人。他认为自己是基尔凯郭尔的回声。基尔凯郭尔是丹麦的哲学家,距今两百年前的人物,基尔凯郭尔认为他的回声在苏格拉底。所以我们从苏格拉底说起,苏格拉底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自知其无知。他把自己认定为没有知识的人,以致他就有了一个提问的特权,好比小学里上课,小学生无知,就可以提问。提问是无知者的特权。所有被苏格拉底提问的有知的人,最后都自相矛盾,要么哑口无言,发现自己的知识并不是那么回事。苏格拉底的破坏力就在这里。一个自认其无知的人最后把人类的知识给动摇了,这说明苏格拉底有诡计。但他这样做,是为了寻找真理,真的知识,这是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他的诡计。所有有知者积累起来的知识大厦,在他的诘问之下,这些知识不能自圆其说,若是倒塌的话,他可以认为,这些不是真的知识。他似乎在嘲弄已有的知识,而千年以后的我们也似乎认同他,所以要从头开始。
两百年前,基尔凯郭尔在德国解说黑格尔的体系哲学,他是个富商的儿子,作品出不出版无所谓,可以自己出。他也反对教会,是个叛逆者。当他从黑格尔那里解脱出来以后,他就重新发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基尔凯郭尔这里,就变得富有现代气息,有了新的回声。苏格拉底的回声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他在柏拉图那里就有回声。我们现在看到的苏格拉底,多数出于柏拉图整理之故。但在基尔凯郭尔这里有了新的面貌。譬如《人类学》这本书给予你们的一个回声,就是我有个影子落在你们身上。这是你的解释,这是他的解释,你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推断康赫这个人,苏格拉底也是这样。通过柏拉图,通过基尔凯郭尔,我们得到不同的解释。基尔凯郭尔如是说到:“苏格拉底把世人从一切实质性中驱逐出去,就像把遇难乘客赤条条地赶出沉船一般;他推翻实在性,在远处窥见理想性,触及它却未能占据它。”苏格拉底使用的语言也非常不可捉摸,飘忽不定,你不知道他什么意图,基尔凯郭尔把它定义为反讽,他说:“这里我们看到反讽是无限绝对的否定性。它是否定性,因为它除否定之外,一无所为;它是无限的,因为它不是否定这个或那个现象,因为它借助于一种更高的事物进行否定,但这个更高的事物其实并非更高的事物。它是一种神圣的疯狂,像帖木儿一样肆无忌惮,不把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就是反讽。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世界历史性的转折点都必定具有这种思想潮流。”
基尔凯郭尔接到一个苏格拉底的声响,然后发出自己的声响,这个声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回声。通过自我表达,以自己的方式传出去。我们把基尔凯郭尔当作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源头。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他的声音,但那时的人们并不能理解。他说结婚你会后悔,不结婚你也会后悔,结婚或者不结婚,两样你都会后悔。要么你结婚,要么你不结婚,你都会后悔。这种语言我们会觉得啰嗦,但在翻译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回事,原本就是这样,这种重复在他的文章中不止出现一次,而是一而再地出现,比如你去为世界上荒唐的事情而笑,你会后悔;你去为世界上荒唐的事情而哭,你会后悔。你去为世界上荒唐的事情而笑或者而哭,你都会后悔。要么你去为世界上荒唐的事情而笑,要么你去为世界上荒唐的事情而哭,两样你都会后悔。其实他表达的就是一种不适,语义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这种语义重复的行为变得重要。他一有机会,就把这种句法套用到文章中去,反复地这么写,这样的不适伴随他的一生。他写了一本《诱惑者日记》,写他勾引一个女孩是为了和她订婚,和她订婚是为了解除婚姻,和她解除婚姻是为了爱情,最后她把女孩献给了上帝。在他看来,订婚就变得世俗,世俗则没有爱情。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在另外一段基尔凯郭尔的话里,更加表露无遗:“我彻底不愿意,我不愿意骑马,那是太剧烈的一种运动;我不愿意走路,那太花费工夫;我不愿意躺下,因为如果我躺下,那么我将继续躺着——这我不愿意,要么我将重新起身——这我也不愿意。总而言之:我根本不愿意。”
卡夫卡的魅力永远都是灰暗的魅力
苏格拉底作为自知其无知的智者是非常有攻击性的,但到了基尔凯郭尔这里,他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的状态,徒劳或者“烦”,就到了存在主义这里。寻找就是欲望的运动,寻找什么,但又得不到,就烦。海德格尔说“烦是生存的本质”,“烦基于巡视”。美国为什么烦,因为老在哪里巡视伊拉克。譬如我想要一个相机,它就会钻到我的意识里来,睡梦中来,不论它离我多远,都离得很近。不论你找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在精神上总是离你最近。在卡夫卡那里,基尔凯郭尔有了新的回声。卡夫卡延续了基尔凯郭尔的不适和徒劳,但他更加强烈。他不像基尔凯郭尔是个富商的儿子,所以他不得不在银行工作。他总要养活自己,没有时间来做专业作家。在我们看来,成为一个专业作家的卡夫卡可能不一定让我们喜欢,因为卡夫卡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古典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有些没完成,现在我们看来都很好。在他则是不幸的事情。卡夫卡的婚姻也是草草了事,跟基尔凯郭尔很相似,他想成为那样的人,反叛者,但他做不到。在他身上,只能是更加地失落。苏格拉底诙谐,老提问;基尔凯郭尔还有勇气,反抗教会和哲学体系。卡夫卡更加下沉,行文中总有稀奇古怪的玩笑,局部文字里有闹剧,不可思议的情节,总体上还是他对自己有一个不幸的感觉。他说基尔凯郭尔是个明星,“他所在的地方是我够不着的”。不只是思想上,还有家庭背景等等。
卡夫卡的工作正是在他够不着的地方开始,这是对事物的回响,也是他非常可贵的地方。所有的声音也是从那里开始,伴随不适,劈头盖面过来,长时间毫无进展,在他看来,这种回旋不定里有一种乐趣。卡夫卡极其专注地咀嚼他所面临的荒诞和可悲的情节。当他反复咀嚼的时候,又充满戏剧的色彩。卡夫卡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我的这本《人类学》里有一段话可以看作对他的一个回声:“他深陷于黑暗,并乐于观察他所深陷的黑暗。他是黑暗的肯定者,在黑暗中探寻黑暗的多样性。他对自己的黑暗之旅充满欣喜,但绝非源于我们通常所见的受虐的快感。因为受虐式的快感仍然依赖于黑暗辩证法赠送的救赎的希望。他有犹太人的黑暗史,但不像犹太教那样把黑暗当作人类之恨的源泉,也不像基督教那样把黑暗当作生命的否定性和用以引渡此否定性的完美的上帝之爱的依据。他以尼采式的肯定面对叔本华式的黑暗,却远比两者的简单混合来得奇妙。”
卡夫卡给我的感觉是,无论你有多少欢快的时辰,他的魅力永远都是灰暗的魅力。回过头来看,苏格拉底辩论的地方是开放的广场,一个老头光着脚,拖鞋也不穿,向那些有知的人提各种问题,这种智者风范甚至有点搞笑,自得其乐,不可捉摸。传到基尔凯郭尔这里,变成一种书房里的“自得其乐”,基尔凯郭尔放弃了空间里的创造性。再传到卡夫卡这里,反讽不再指向任何东西,而是指向自己,好像反讽就是反讽的目的。譬如卡夫卡的《城堡》,他自己根本没有兴趣进去,他待在那里,处在不适当中,就是他的目的。他没有真的那么想去城堡。基尔凯郭尔还有哲学这个东西,但卡夫卡一直在原地玩,两个仆人或者酒吧老板,情感也奇怪,他在奇怪的关系里找到乐趣,这是暗夜里的回响。卡夫卡读多了,整天在幽暗的山谷里待着,听到稀奇古怪的笑声,带来身体和精神的不适,那些东西是我要的,没错,但我现在够了。我需要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看到太阳,另外一个声音传过来。“空气!更多的空气!”这是尼采的声音,他反对是颓废的声音,他反对的那本书就叫《瓦格纳事件》,这是我的另外一条回声的线,“瓦格纳受之于叔本华的恩惠真是不浅。唯有颓废哲学家才使颓废艺术家获得了真身。当这颓废者损害我们的健康并且损害我们的音乐时,我不能袖手旁观!说到底,瓦格纳是一个人吗?难道他不更是一种疾病?”尼采的身体也很不好,但他不想找到皈依,精神想要宁静,一定要到山顶上面,太阳下面。然后他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第一要求和最终要求是什么?是征服自己的时代,成为永恒。那又用什么来做最大的斗争呢?自己成为时代孩子的一切。他把自己定义为时代的孩子,瓦格纳也一样,他们都是颓废者,但尼采正视自己是个颓废者这一事实,并且与之抗争,但瓦格纳不是。
鲁迅面对虚无的时刻,在无物之阵中举起投枪
二战以后,西方的作品我看得非常少,我认为欧洲精神在这之后处在死亡、半死亡状态,那边有一道音墙竖立在那里。随着纳粹的覆灭,为了安全起见,代表欧洲精神最无畏的东西也都衰亡了。以前,欧洲哲学家的思想是没有边界的,可以一往无前地走;二战以后,思想有一个限度,到纳粹为止。战后德国没有堪称宗师的哲学家,但之前他们这个地方可是人才辈出。纳粹毕竟是人类的行为,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今天我们对纳粹本身也没有进行更好的思考。
所以我们要问“路在哪里”,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今天说语言意识从哪里来,你会发现它不是单独冒出来的。语词基于语句,语句基于语境,语境基于语言,语言基于语言的回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鲁迅所说的话。我们说“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第一层意思可以是鼓励式的。转到第二层意思,语调发生变化,那就变作一种随大流的讽刺。然而当讽刺里的刻薄劲儿一旦消除,那就转入第三层的意思,成了反讽,是对讽刺的讽刺。万事看开,有自嘲的成分,有奇怪的语意,有点解脱,自我安慰,接受失败,没有攻击性,更加豁达。通常是随遇而安,但是难免还有一点油腔滑调,问题是我们感到鲁迅不是一个油腔滑调的人,他既不在第一层的意思里,也不在第二层的意思里,第三层的意思也跟他不沾边。这句话的语境我们又可以从另外的语句里得到回响“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这是《故乡》这篇前面的话,因为“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所以鲁迅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反讽之外的一个情况,是剥离这三层意思之后赤裸裸的事实,他不是反讽者,他是把这些意思赤裸裸地呈现给赤裸裸的人面前,再来看“其实地上本没有路”,鲁迅就是从赤裸裸的事实开始。
写《故乡》的时候,时在一九二一年。四年以后,鲁迅写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是连绝望也否定。既不承认希望,也不承认绝望,譬如他写到两个战士,坐在那里没有动,但刀光剑影很厉害,一直在打,绝望、希望两者都是虚妄,这就是鲁迅面临的虚无的时刻,他没有寻求佛教来解脱,而是投入无物之阵,在无物之阵中举起投枪,在无物之阵中衰老。二战以后,日本学者为什么在鲁迅这里找到力量,就是他们看出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主体的问题,主体越强烈,就越想要去抓住希望或者绝望,反抗什么东西,问题也就随之出现。最后可能跟对方是一样的。但鲁迅给出的态度,在他的另一篇《雪》中可以见出,他如是写到“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然而“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日本学者在此得到了一个回声。一如白居易写给元稹的《舟中读元九诗》所示: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这就像火把在黑暗的山谷亮起,火的出现,才让我们知道黑暗有多大。我的火也是先人传给我的,我愿意把我的火种传给你们,然后从你们的身上辨认出我自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
【康赫简介】
浙江萧山沙地人,垦荒者和流浪汉生养的儿子,1993年8月开始居住北京,经数度搬迁,从王府井来到了回龙观,随后从老家接娶了妻子,随后又有了一个儿子,其间换过许多职业,家庭教师,外企中文教员,时尚杂志专栏作者,大学网站主编,演出公司项目策划,地理杂志编辑,日报记者,戏剧导演,美食杂志出版人,影像设计师,样态设计师,当代艺术鞭尸人,由实而虚,直至无业:一位从不写诗的诗人。“北京尤如沙地,是流浪汉们的故乡。”他说。因而他的命和他的父母一样,是垦荒。
出版长篇小说作品《斯巴达: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 《人类学》;戏剧作品《纣王》 《审问记》 《采访记》 《泄密的心》 《受诱惑的女人》 《陌生人》 《北京杂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