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争吵中的哈萨克人,只要有一位引用阿拜的诗句或箴言来说服对方,冲突便会戛然而止,双方很快就会握手言和。这种情景,在哈萨克草原上并不鲜见。”
这是诗人沈苇所著《新疆词典》的第一个词条“阿拜”的开头,这本词典一共囊括了关于新疆的111个词条,涉及十几种文体。
沈苇本是浙江人,但他在新疆一呆就是27年,他曾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青,向往边疆,常常脑子一热,带上简单行李,怀里揣很少一点钱,坐上绿皮火车就远行新疆、西藏而去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大多热爱北上广,喜欢大城市,喜欢到‘中心地带’去当‘沙丁鱼’。这是两种不同的时代氛围。”而他调侃自己是以“迟到的盲流”和“无知者”的身份闯入新疆的。
他在新疆做过教师、记者,现为新疆作协专业作家,《西部》文学杂志总编。“如果我不离开浙江,不离开江南,不去新疆,也会写诗,但我的写作肯定不是目前这种状态。”
蓄须让沈苇看起来有点新疆人的感觉,不过陈丹青对他说:“你看起来还是南方人。”关于蓄须,沈苇还有一个好玩的说法:“我发现大部分留胡子的人比不留胡子的人要害羞。”
现在回到浙江,别人都认为他是新疆人,而在新疆,别人又觉得他是南方人,说不定哪天就离开了。不过沈苇认为这种身份分裂感和尴尬挺真实的,倒不是坏事情。
沈苇觉得在这二十几年中,新疆和自己是相互的捕获者。“第一故乡给了我启蒙,第二故乡给了我启示、教诲。我是新疆的新移民。移民是试图与远方、与异乡结合的人,而异乡无疑是移民最好的、也是谦卑的课堂。”
这两年沈苇也有往内地调动的机会,但他都放弃了。一方面是情感的因素,“情感是跟时间有关的,你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你对它的情感就越深,所谓日久生情嘛。写作正是从这种情感中一点点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新疆还在吸引他、捕获他,“我觉得还没待够,即使暴恐事件也没把我赶走。”
沈苇说,在新疆生活的一个有福之处,在于可以欣赏自然、人文、民族等各个层面的差异性。抹去了这种差异性,新疆就不能称之为新疆了。在新疆文学界,有很多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双语作家,沈苇平时和他们交流较多,同时他主编的《西部》文学杂志也在不断发掘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
在沈苇来上海参加活动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新疆词典》的写作和新疆的多元文化等问题专访了沈苇。

诗人沈苇
新疆的魅力在于差异性和多样性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新疆表达”的说法,它具体指什么?
沈苇:老实说,新疆还没有找到自己最好的“表达”。因为表达上的失语状态,使其主体性和内在的真实性没有得到很好呈现。新疆以前用的旅游宣传口号是“魅力新疆”,然后我到网上一查,发现全国从省到地区到县到乡到村有300多个“魅力XX”,这就等于什么都没说。
“魅力”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再用到新疆身上其实是在矮化新疆、遮蔽新疆。一说起新疆,我们总想到“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等,把新疆变成审美消费的对象,却唯独忘掉了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我曾在一篇访谈中讲到,对于新疆,与其一味强调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的,还不如多讲讲“人”。“人民”不是个抽象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在边疆,哪有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的,只有一个个的人、一颗颗的心啊。当文学越过民族的边界,就能找到属于人的表达。
关于新疆,我在《新疆词典》里提到了几种表述:我曾称新疆是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南疆北疆都是它的页码,沙漠绿洲雪山草原都是它的文字。我也曾称它为“启示录式的背景”,世界上三大宗教,有两个就是产生在沙漠背景中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一词拉丁文的原义就是“恐惧”,人有恐惧,就会寻找上帝,就有了信仰。人处在戈壁沙漠中,在荒凉的大背景下就会有坚定的信仰,也会有强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上帝是公正的,他将一块土地变成沙漠,变成不毛之地,但同时将石油、天然气等藏在了地下,地下有宝藏,所以我认为新疆虽然表面上是荒凉的,但它骨子里的文化是灿烂夺目的。这也是一个表述。
《新疆词典》没有前言和后记,所以这次我来之前特别写了两首短诗作为前言和后记,这也可以当做我对新疆的表述吧。前言我写了三句:“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本书,她愿意成为我的一本书吗?因为它已是大地的心经和原典。”后记我写了两句:“我找到了爱她的111个理由,同时得到了166万平方公里的忧伤。”
我们再来谈一谈新疆的精神状态。我想到一个词——正午。新疆的精神状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午时分的寺庙拱顶,同时结合了生命和死亡、阳光和阴影。新疆历来在政治上与中原关系密切,但在精神气质等方面,西来文化对它的影响很大。生活在新疆,饮食、人的举止个性、思维方式等方面有某种欧洲特点,甚至带有一点土耳其、希腊、印度和阿拉伯的味道。我们常说新疆是四大文明融汇的地方,塔里木盆地是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现实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新疆位于古地中海的边缘,就是地理学中的特提斯海,因为大陆架运动,后来古地中海慢慢萎缩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我觉得这股地中海的精神一直融在新疆的血液里。在《新疆词典》最后一篇“正午”中,我提到过这种正午的积极态度,不像现代人一味地通过病态、畸形和虚无的东西来反抗。加缪将地中海精神称之为“正午的思想”,他说:“如果说,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崇高的悲剧,而不是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
所以说,我们讲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归根到底还是在讲人,虽然我知道现在好多人到新疆,首先还是受到地域的感官冲击,一种自然的震撼。所谓的新疆精神,所谓的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就是一种反抗虚无和死亡的精神。从这一点上讲,虽然现在新疆的处境有些艰难,但是我对新疆的未来不绝望。新疆绝不是“暴力”的代名词,那里的人们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吃饭、睡觉、生儿育女等等,这种日常性才是更为真实的存在,它是不可颠覆的,就像天山、昆仑一样不可颠覆。请问,谁能颠覆天山、昆仑?
沈苇:内地文化是很单一的文化,有时候在江南待着跑来跑去,每个地方都差不多。新疆的魅力在于差异性,民族之间、文化之间、习俗之间的差异,这种东西是非常有魅力的。差异性如果被抹杀的话,新疆也不是新疆了。差异性给新疆文化带来一种混搭色彩,新疆文化是一种混搭文化。混搭文化是很有魅力的文化,就像女孩子喜欢波西米亚风格,它就是身体上、衣饰上的混搭文化。拉美就是混搭文化地区,所以拉美才有印第安文化和殖民文化的糅合,最后产生了拉美文学爆炸。古丝绸之路也是混搭文化,地中海地区也是,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
混搭文化很有魅力,你感觉到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可以互为镜像,互为映照和参照。在混搭文化里你可以找到很多参照系,这种参照系可以延伸到印度、希腊和罗马文化,可以延伸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体系。尽管混搭出来的是一个小地方、偏远地方,但是延伸出去的东西太多了。混搭文化几乎代表着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我觉得它对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
澎湃新闻:混搭文化是不是只有诗人的细腻才能敏感地体会到?
沈苇:不单单是写作者,生活在那里的每个人都能受到启发和影响。长期生活在一片土地上,文化之间的交融、相互影响,普通人也能感受到。比方说,很简单的,汉族人会去吃维吾尔族的馕和烤肉,吃哈萨克族的手抓肉,喝蒙古族的奶茶,饮食就是一种对话和交流。
新疆的汉族人受了很多少数民族生活习性的影响,他们好客直爽、感性热情,就是受少数民族影响的,新疆汉族和内地汉族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在新疆,大家一起吃饭很有仪式感,南方好像没有这种仪式感。在新疆吃饭前,请客的人一般要站起来发表演讲,汉族人吃饭也是这样的,关于“今天为什么要请客”,要发表头头是道的演讲。
吃完饭,在南方好像就一哄而散了,而在新疆,一定要请一个身份地位高一点,最好年龄大一点的人发表总结,把每个人都要点评到。我遇到过一个在喀纳斯景区工作的朋友,他写诗,会唱歌,可以现场把每个人的特点汇集起来编成一首歌,把客人的长相、职业、性格特点等编到歌里去,最后唱一遍作为总结。
新疆人喝酒比我们江浙要文明、浪漫,我们江浙人最后一点酒要倒给一个领导或一个老板,叫发财酒,新疆的最后一点酒要倒给长者、女士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叫幸福酒。幸福比发财更重要、更高级,发财的人不一定幸福,幸福的人可能很穷,但他就是幸福。喝酒的这个仪式,新疆人无疑比江浙人有文明高度。这也是日常的文明,各民族之间相互受影响。
澎湃新闻:那这种混搭文化是不是只有异乡人才更容易感受到?
沈苇:不一定的,因人而异。异乡人在今天是指移民、外来者。但我恰恰看到很多外地去的人对新疆的描述经常是浮光掠影的,甚至是以讹传讹的。当然本土的人,由于生活时间长,容易引起感受上的麻木和迟钝。作为出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确需要一点跳出地域看地域、跳出自己看自己的勇气。
作为外来的人,即使你是一名游客,也应该更多深入了解新疆,不要只是看新疆的风景,看大山大水,也要了解民族的心声,与人接触,才能有更大的观察和收获。现在常有内地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经常到新疆生活一段时间,住在村子里面,这样就有深入、细微、真实的体悟。
澎湃新闻:南方人到新疆和新疆人到南方会不会有利于打破文化边界?
沈苇:对。人的第一故乡无法选择,父母无法选择,出生的村庄无法选择,但是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人在地域变迁和文化反差中受益无穷,会从单一的人变成多维度的、开放开阔的人。当然变迁中也有冲突,不可回避的文化冲突。
比如内高班(编者注:内地高中班,让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他们在新疆有的初中毕业一句汉话都不会说,他们到内地要先学汉语。内地这些城市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新鲜的地方,他们要适应,要和汉族人接触,困惑和冲突是必然的。但人是可以沟通的。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内高班的报告文学集,内地的汉族人、老师为了那些孩子真是付出了好多心血。这种沟通我觉得是可能的,交流也是必须的。
我认识一个维吾尔族男孩,现在是我的诗友,叫麦麦提敏·阿卜力孜,1992年出生,他是和田地区皮山县的一个孩子,初中毕业就到北京通州的潞河中学学习,潞河中学是全国第一所办内高班的中学。他去的时候一个汉字都不会写,一句汉话也不会说。但几年下来,他遇到了很好的老师,他的班主任在北京好像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培养他用汉语写诗。他现在在江苏上大学,今年应该毕业了,已经出了两本汉文诗集,还获得了我们《西部》杂志的“西部文学奖”。对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维吾尔族诗性思维和优雅的汉语言结合起来后,造就了一匹诗歌黑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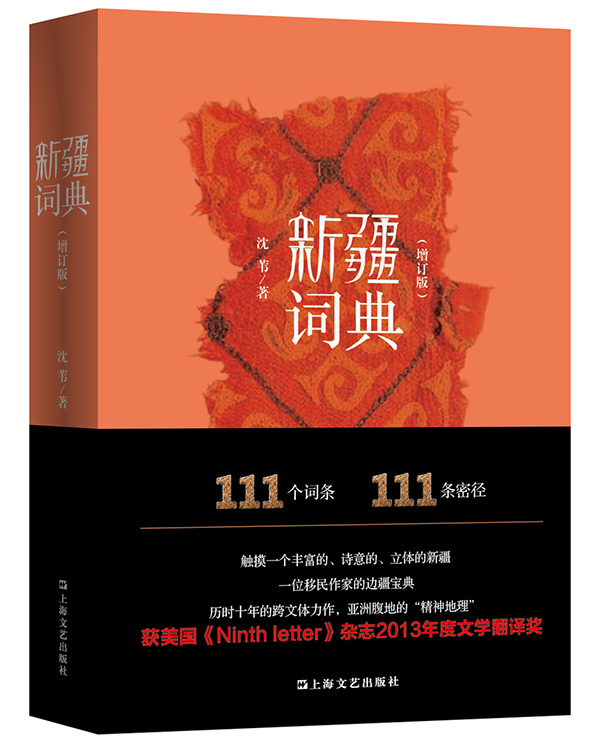
《新疆词典》,沈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10月版。
写作者需要打破文化和语言的界限
澎湃新闻:《新疆词典》中的词条是您事先规划好的还是之前文章的汇编?
沈苇:其实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因为我的写作主要是诗歌,散文对我来说是诗歌的延伸和拓展,也是诗歌之外的一种表达和补偿。持续写诗就像在建一座城堡,我在这座城堡旁边盖了一个房子、一个驿站,它就是《新疆词典》。它提供了理解新疆、进出新疆的一些通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跨文体的写作。因为我对目前散文的写作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约瑟夫·布罗茨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诗人和散文》,他认为一个诗人在散文中学不到什么东西,但相反,一个散文家在诗歌里可以有很多的收获,比如说专注力、凝练和警觉高涨的情绪等。
而且我发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特点,在我接触的小说家里面,一流小说家是喜欢诗歌的,会读诗,探讨对诗歌的感觉,二流小说家则对诗歌没有感觉,三流小说家排斥甚至是痛恨诗歌的。我上次在广州参加“花地文学榜”的颁奖典礼时碰到了毕飞宇,他的短篇小说是很出色的。他说自己短篇小说的灵感几乎全部来自于诗歌,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
还有就是现在散文的写法越分越细,有一种不好的“专业化”、“分类化”倾向。古人只有“诗”和“文”的区分,诗歌之外的文体都属于“文”,包括笔记、话本、杂剧、小说等。而我们现在散文的“文”分得越来越细了,就像大学里的分科一样,有理科、工科和文科,各科里面也分不同的系和专业,例如我女儿在大学的生命科学院就读,光生科院里面就有三个专业: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制药。我问她这三个专业有什么区别,她说大同小异。分得太细了。散文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通过这本书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我在诗歌写作中提到“综合抒情”和“混血的诗”的说法,讲求的也是综合性。当然边界在文学中是存在的,在文化中也是存在的,甚至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新疆词典》的写作体现的是一种跨文体的追求,就像现代学科里的“超文本”概念,当然这也是越过语言边界的一种努力。新疆有52个民族,我们需越过各民族的边界找到一种超越个人经验、体现他者自我化的言说,也就是“为他人”的言说,这是文学的基本伦理。作为作家的那个“我”,不单单是一个作为自己的“我”,“我”身上还可能活着他人的灵魂甚至动植物的灵魂、大地和星空的灵魂。
沈苇:我们再来讲一讲“混血的诗”,我一直觉得诗歌是一种阴阳并济、雌雄同体的艺术。“西部文学”这个概念太符号化了,什么“雄壮”啊、“豪迈”啊,其实西部既可以是太阳照耀下的阳刚的西部,也可以是“明月出天山”意境下阴柔的西部。
我在新疆生活了27年,有时会感觉到光凭诗歌来表达新疆已不够了,需要其他一些文体的努力,来激发我、推动我。包括办杂志也是以“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为办刊宗旨,谋求地方性和国际化的结合。所谓地方性,就是《西部》杂志要立足西部,国际化则是指一定要有国际视野,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除诗歌之外,我还写了一些舞台艺术作品如歌舞诗等,就是想从多方面来呈现新疆。
澎湃新闻:在新疆待了二十多年,您有身份认同的焦虑吗?向别人介绍自己会说自己是浙江人还是新疆人?
沈苇:有尴尬,有冲突,有矛盾,但都挺真实的,不是坏事情。会有这种情况:回到浙江,他们不承认我是浙江人,说我是新疆人;到了新疆,他们又说我是南方人,说不定哪天就离开了。在他们的种种“假想”中,我就变成悬空的、没有立足之地的人了。
我写过一首诗叫《两个故乡》。但我现在觉得两个故乡已不存在——浙江和新疆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了。从现在的生活来说,空间的概念已经不太重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往返新疆坐火车,四天三夜,81个小时,有时候坐票买不上还要站上一两天。林则徐当年发配伊犁充军,从北京到伊犁走了一百天,放在那个时候,我要是一去新疆可能一辈子就见不到父母亲了。
现在回浙江一趟很方便,我早上早点出发,坐飞机到虹桥机场,然后再坐车回家还赶得上吃中饭,半天就到了。现在,人的距离不在空间上,人的距离在心里,空间已不是距离概念。说到前面《异乡人》这首诗,我是移民,移民就是异乡人,是“他乡的隐形人”和“故乡的陌生人”。古人回到故乡是“物是人非”,小时候的房子、种的树都在,但是人都变了,上一辈去世了,同辈变老了。现在叫“物非人非”,环境被彻底改变,乡村被连根拔起,人真正的故乡回不去了。
故乡是人随身携带的东西,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着语言和诗歌。母语是写作者最后的故乡了。我曾说自己得了西部和江南的地域分裂症,我是一个有裂痕的人。《异乡人》那首诗里说,自己就像一只破皮球,被江南和西域两只野蛮的脚踢来踢去,但这样并不痛苦。成为这样一个人,既是分裂的,也可以通过写作去治疗的。通过地域分裂、文化分裂甚至内心分裂,我更热切地去寻找一种完整性。
(陶越彦、李静云亦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