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沈从文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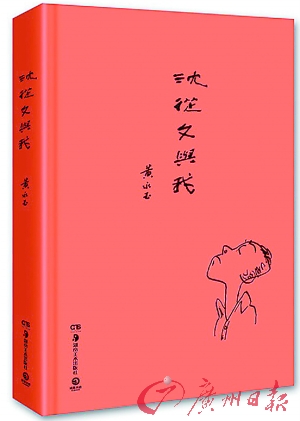
13
黄永玉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新书摘
内容简介
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在黄永玉的生活中,表叔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表叔那种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亲情、故乡、身份……多种因素使得他们两人交谈颇深,哪怕在艰难日子里,往来也一直延续着。
沈九娘
听我的母亲说,我小的时候,沈家九娘时时抱我。以后我稍大的时候,经常看得到她跟姑婆、从文表叔诸人在北京照的相片。她大眼睛像姑婆,嘴像从文表叔,一头好看的长头发。那时候时兴这种盖着半边脸的长发,像躲在门背后露半边脸看人。我觉得她真美。右手臂夹着一两部精装书站在湖边尤其好看。
我小时候,姑婆租了大桥头靠里的朱家巷有石板天井的住处。常陪姑婆聊天的有两个,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聂姑婆她妹妹的儿子,外号叫“聂胖子”的,也是我爸爸的表弟。
九娘那时候不在,她一定是跟着从文表叔已经在北京大学了。九娘在北京跟表叔住了好些年。很难说当时由谁照顾谁。料理生活,好像都不在行。从文表叔对饮食不在乎,能入口的东西大概都咽得下去。而九娘呢?一个凤凰妹仔,山野性格,耐着性子为哥哥做点家务是难以想象的,只好经常上法国面包房。
她当时自然是泡在哥哥的生活圈子里,教授、作家、文学青年、大学生、报社编辑、记者、出版家川流不息。她认真和不认真地读了一些书,跳跃式地吸收从家中来往的人中获得的系统不一的知识和立场不一的思想。她也写了不少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一时有所悟,一时又有所失,困扰在一种奇特的美丽的不安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九娘的性格,只是运气好,加上是个男人,有幸得以逃脱失落感的摆布。
她一天天地长大,成熟,有爱,却又无所依归。如《风尘三侠》中之红拂,令人失之迷茫。有的青年为她带着幽怨的深情远远地走了,难得有消息来往;有的出了国,倒是经常捎来轻浮而得意的口信。她抓住的少,失落的多。
这时,从文表叔结婚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哥哥身边忽然加入了一个比自己更亲近的女人,相当长期的生活突然名正言顺地起了质的变化,没有任何适当而及时的、有分量的情感来填补这迫切的空白。女孩子情感上的灾难是多方面的。
我完全不能理解年轻的表婶在新的家庭里如何对付这两个同一来源而性格完全不同的山里人。表婶那么文静。做表侄儿的我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几十年来只听见她用C调的女声说话,着急的时候也只是降D调,没见她用常人的G大调或A调、B调的嗓门生过气。我不免怀疑,她究竟这一辈子生过气没有?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就细心地观察体会,在令她生气的某种情况下,她是如何“冷处理”的,可惜连这种机会也没有。这并非忍耐和涵养功夫,而是多种家庭因素培养出来的德行和教养,是几代人形成的习惯。她一跨进沈家门槛就要接受那么严峻的挑战,真替她捏一把事后诸葛亮的汗。
抗战使九娘和往昔的生活越离越远,新的动荡增加了她的恐惧和不安。巴鲁三表叔正在浴血的前线,姑婆和姑公都已不在人间,云麓大表叔是一位不从事艺术创造的艺术家型的人,往往自顾不暇。当发现九娘的精神越来越不正常的时候,送她回湘西倒成为较好的办法。
九娘从昆明回到湘西的沅陵。他们兄弟在沅陵的江边以“芸庐”命名盖了一座房子。沅陵离故乡凤凰百余公里,是湘西一带的大城之一。乱离的生活中,我的父母带着除我以外的四个孩子都在沅陵谋生。当然,“芸庐”自然而然地成为亲戚活动的中心。巴鲁表叔那时正从第一个激烈的回合中重伤回来,也住在沅陵养伤。眼见送回来的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妹妹,不禁拔出枪来要找从文二表叔算账。他是个军人,也有缜密思考的经验,但妹妹的现状触动了他最原始的情感。妹妹呆滞的眼神、失常的喜乐、不得体的语言是一种极复杂的社会化学结构。有一本名叫《精神病学原理》的厚厚的大书第一句就说:“作为社会的人,每一个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精神病。”像社会发展和历史可以触发出“天才”一样,也产生着精神病患者。事实上天才和精神病者之间,只不过隔着一层薄薄的病历。每一个人只要冷静想一想都能明白九娘精神分裂的社会和生理缘由。巴鲁表叔从此也沉默起来,不久又奔赴江西前线去了。
九娘的病在偏僻的山城很难找到合适药物。抗战的沸腾令她时常上街闲荡,结果是身后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闲人。云麓大表叔和我的弟弟担当了全城寻找九娘的任务。直到有一天,九娘真的应验了从文表叔《边城》的末一句“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的谶言,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九娘。在沅水的上游有一个遥远的小村,名叫“乌宿”,河滩上用石头架着一只破船。九娘跟一个破了产改行烧瓦的划船汉住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生的儿子已经长大。
多少年来,在从文表叔面前,我从来不提巴鲁表叔和九娘的事,也从不让从文表叔发现我清楚这些底细。从文表叔仿佛从未有过弟弟妹妹。他内心承受的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所写出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悲剧性。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